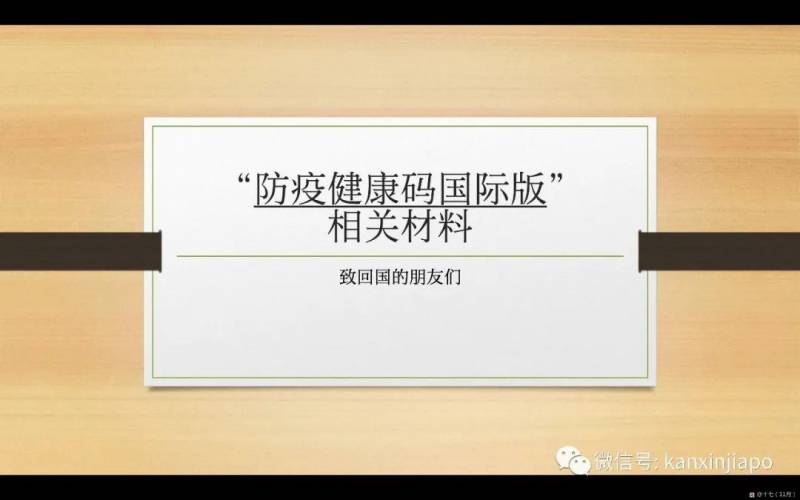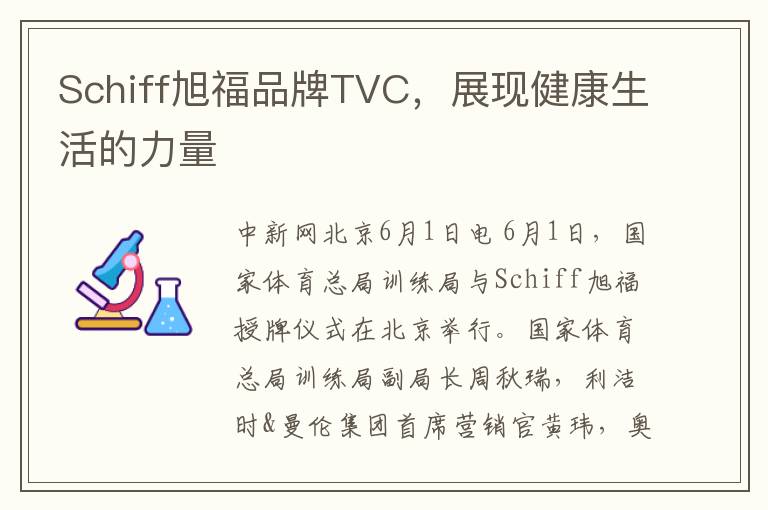——纪念我的同学高云龙
马志华(北京大学法学院1996级本科,达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对我而言是个非常纠结的日子。用弘一法师的话说:悲欣交集。

一
当天上午十一点四十分,我的幼子诞生在秀丽的南方小城柳州的一个晴好的日子里。从凌晨三点我被妻子从睡梦中唤醒被告知她已破水,到我看着妻子怀抱着这个初生的小脸儿红彤彤的婴儿被推出产房,我似乎并没有经历那传说中的慌乱、兴奋与激动,但却在陪护我妻子待产的几个小时里靠前次目睹了一个母亲为诞下一个新的生命所需要经历和忍受的巨大苦痛。
那时她躺在待产室的病床上,周围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此起彼伏,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而她正被一阵猛似一阵的宫缩带来的剧痛所折磨,气力耗尽,几乎奄奄一息。每当剧痛袭来,她便用手紧紧地抓着我,指甲几乎要嵌入我的皮肉。但我除了轻轻擦拭她被汗水浸透的肢体,除了用不久前学来的一套什么拉玛泽镇痛法指导她呼吸,除了不停地跟她说什么“加油”“忍住”“坚持”,却再无任何用处。我只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眼睁睁的看着她承受这痛苦,却束手无策。
在此之前,我从书上看到过,因为女性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被赋予了孕育后代、负责生产的责任,她们具有比男性强的多的对疼痛的忍耐能力。我也听说过,按照医学上的分级,生产时母亲所经受的疼痛是十二级疼痛,也就是人类能够经历的最终级别的疼痛。但直到我进入陪产室的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些描述究竟说的是什么。我于是靠前次知道,在每一个添丁的喜讯背后,那位母亲都忍受了怎样的折磨。每一个母亲都是伟大的,我向你们致敬。
然而我们的孩子终于还是顺利的降生了。紧闭的双眼,精致的鼻子,小巧的嘴巴,乌黑浓密的头发,胡乱伸展的小手和脚丫。一切都从他到来的那一刻归零,一切都从新开始,一切都再也不同了。这真令人欣喜。
我彼时疲惫地靠在护士站的台桌,正在遣词造句,准备发出一条微博公布喜讯,然而登陆后却发现我被一个大学同学圈到,他的那条微博写到:“Dear my of PKU 96 Law, Mr. Gao away. It is very very sad. My God, he is so young. .” 高云龙去世了!
这是个令人震惊而悲伤的消息。很多人说他们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我也是。


二
高云龙是我在北大四年的本科同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那一级喜欢把三个字的名字压缩成两个字来念。所以我在年级里被叫做“马志”,同样,我们都把高云龙叫做“高云”。
高云是黑龙江佳木斯人,说一口带地道东北话。我记得我大一刚认识他的时候问他冬天佳木斯有多冷,他说零下三十多度很正常。说三的时候,他用的是二声。
高云在我的印象里自始是很圆胖的,偶尔会留一点小胡子,发型是亘古不变的平头,大学四年的时候是,我两年前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还是。他不是我们班的,他的宿舍因此也离我的较远。我们的关系算不上紧密,接触也并不很多。真的,我发现我对他毕业后情况大部分是听说的,甚至是这两天才从微博上看到的。
无论是从学习成绩上还是后来的律师职业发展上,高云都是我们年级最优秀的。没有之一。我们九六级本科普通班学生一百二十人,男生四十,女生八十。大学四年下来,总成绩前十名只有一个男生,就是他,而且是年级靠前。我记得他当时四年必修课(包括像马哲这样的课)平均分好像是九十多分,比第二名那个女生(我已经不记得是谁了)高出一大截子,完全匪夷所思。他本科毕业后继续留校读了龚老师的国际法研究生。又因为成绩年级靠前,其间被北大送到日本东京大学读了一年法学硕士,至北大硕士毕业他已经拿了两个北大的法学学位和一个东大的学位。后来他又去了耶鲁大学读LLM。我觉得他真的已经把中日美三国较好的法学院读遍了。而后他在Shearman Sterling工作了几年,并在三十三岁那年被Baker McKenzie挖去当合伙人。这个消息当年是令我们一班在中外律所里打拼的同学颇为震惊的,因为他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而且他打破了大家心中的那个 “在外所发展无法提合伙人”的定律。我记得我当时着实因此郁闷了好一阵,心里说看看人家高云,自己都是怎么混的啊?!
高云的优秀和出类拔萃,我想,是有必然原因的,因为他即便不是我们级里最聪明的,也一定是我们年级男生里(女生我不知道)最刻苦的。这一点,很多同学在微博上发文悼念他的时候,竟然对他的印象都高度一致:他每天早晨都是最早离开宿舍去图书馆自习的人。他有一个大号的铝饭盒,里面放着吃饭用的勺子。我印象里,他大学期间一直在用一个样式完全过时的几乎是 高云的优秀和出类拔萃,我想,是有必然原因的,因为他即便不是我们级里最聪明的,也一定是我们年级男生里(女生我不知道)最刻苦的。这一点,很多同学在微博上发文悼念他的时候,竟然对他的印象都高度一致:他每天早晨都是最早离开宿舍去图书馆自习的人。他有一个大号的铝饭盒,里面放着吃饭用的勺子。我印象里,他大学期间一直在用一个样式完全过时的几乎是小学生才会用的双肩背书包,而且他走路总是一颠一颠的,这样一来,他书包里的饭盒总会随着他的脚步,有规律的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所以我们大家听到这样的声音,就知道是他。而至少在我住宿舍的那些日子里,无论是昌平园还是燕园,我几乎每天早上都能听到他从宿舍离去的声音,而那时候,我们大部分还都懒在床上睡觉,而当这“哐啷、哐啷”的声音再次传来的时候,我们通常已经熄灯了。说实话,当时我觉得他真的很烦,自己爱读书就罢了,还弄的大家睡不好觉。如果我还有机会见到他的话,我一定要捶他一拳,告诉他:高云,你当年把我们吵的好惨啊!
回想起来,我对高云的了解真的很有限,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生活交集。我在大二回到燕园以后,一直醉心于周围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热衷于参加各种事后看来完全浪费时间的所谓“社会工作”(甚至一度几乎加入校团委),并拖拖拉拉地谈了一场后来令我当时女友伤心欲绝的初恋。而高云则可以说是和我完全相反的人,他的生活在我看来单调、乏味而无聊,因为他只知道读书。他上课永远坐在靠前排,因为只有他才能每天起那么早去跟那些疯狂的女生们抢头排的座位。而且我还觉得他样子很土气。他大一在昌平园的时候老是穿我们年级统一购买的那套兰白相间的肥大的运动服。而回到燕园后,他的装扮变成了一件那种没有领子的只有中年人才会穿的肉色带暗花的开身夹克衫,一条米色或深色裤子和一双说不上款式的运动鞋或是黑皮鞋。加上他的招牌式的平头、“哐啷、哐啷”和一口东北话,我真觉得他更像是个来城里进修的农村干部。而更关键的是我几乎不怎么能见到他,我们的大学生活内容完全不同,选的课后来也不太一样,而他又永远在不知道哪个楼里上自习。即便我偶尔去他们宿舍,他也少有出现,即便见到了,也只是胡乱的打个招呼,并没有再多的交流,直到我们毕业。
他快从耶鲁毕业的那年曾经写信联系过我,向我询问回国找工作的事儿。当时我在一家行将就木的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上海办公室做事,被很多不明真相的同学所羡慕。我忘了当时自己是怎么回复他的了,但总归是没帮上忙,因为他后来去了比我那个所不知道强多少的 。再后来,我们搬到国贸三期之后,有一天周靖说高云龙在大会议室呢。我赶紧过去和他打了招呼。他穿着一身藏青色西装,还是照旧的圆胖,平头,略微有些小胡子,但西装并不很合身。我们简短的寒暄了几句之后,我就忙着回去赶文件了,以致错过了和他的午饭。但有些东西错过了,真的就再没有机会了。留下的只有遗憾。
高云以合伙人身份加入Baker的北京办公室之后似乎一直就没有真正工作过。在那之前,我已经听同学说他在的时候工作过于劳累,以致于心脏出了问题,做了大手术。当时我颇感震惊,但始终没有得到过确切的消息。2011年冬天,一个定居美国的同学回北京出差,组织同学聚会,我找到他的秘书,被告知他在家里养病。我于是问他的手机,她秘书说他不方便接。我当时觉得很蹊跷,什么病能让接个电话都不方便呢?此后好像我们发了短信,我让他注意身体,他说谢谢老同学关心。仅此而已,再无联系,直到我昨天收到他因病去世的消息。


三
在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一个新的生命挣扎着、哭闹着来到了我的生活里,而一个老同学的生命,一个只走过了三十四个年头的精彩的年轻的生命却休止了,离开了,毫无声息。这是怎样的令人欣喜又怎样的令人哀伤呢?
我怀念高云,因为无论我们有怎样不同的人生选择、生活方式或者价值观念,我都曾和他同学一场,我们都曾经在同样的食堂打饭,听同样老师传道解惑。我怀念高云,因为他是我们年级最优秀的人之一,是我们北大九六级法律系本科永远的骄傲。
今天晚上,我独自开车去给我尚未出院的妻子送家人为她煮的鸡蛋酒酿。在这个南方深秋的雨后的路上,我想到高云那背着书包一颠一颠赶往教室的背影,想到那熟悉的“哐啷、哐啷”的饭盒声,竟不能自已,泪如雨下。
就像微博上一个人留言说的,三十多岁的年纪,正是生活中上有老下有小、事业上需要开始独当一面带着一个团队打拼的时候。在这个年纪就抛下家人、朋友独自离去真的太令人难以接受。高云系家中独子,父母健在。但他已不能用自己的努力侍奉双亲了。高云已婚,有一子,年极幼。但他已经不能陪伴他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了。 我毕业后曾用多年时间四处游历,只求增长见闻,丰富阅历。记得少不经事的我曾不止一次在获得新的生命体验后有死而无憾的感慨。现在想起来,那时真的只想到自己。此时的我,家中有正在老去的父母,膝下有刚刚来到人世间的孩子。为了他们,为了我的妻子,我必须健康的活着,不管在哪里,不管做什么,这已经成为我的责任。真的,健康的活着,愉快的活着,珍惜每一天,和我们所爱的那些人。
在一起,无所谓。
高云,我身在柳州,今天不能赶回去和你告别了。老同学,一路走好!
我们北**学院96级本科,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因高云龙同学的离去,顿生伤悲,但是,我们都得坚强,都得更加努力,得更加好好工作,我们的责任是:健康地活着,报效中华!——陈球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