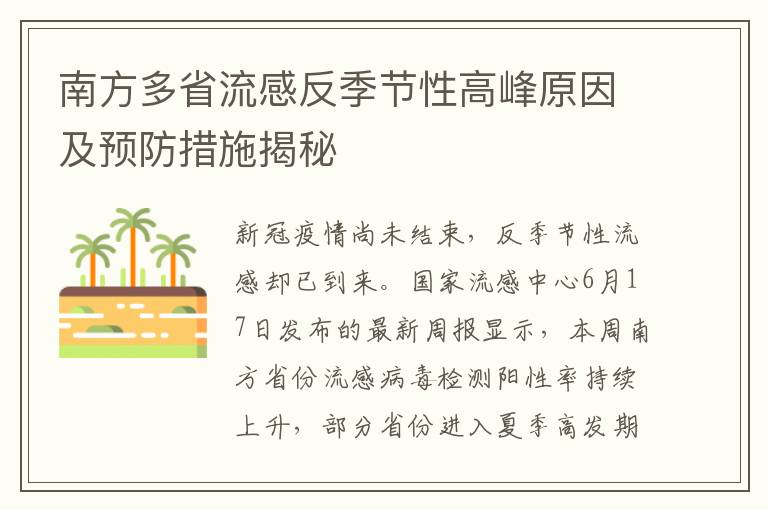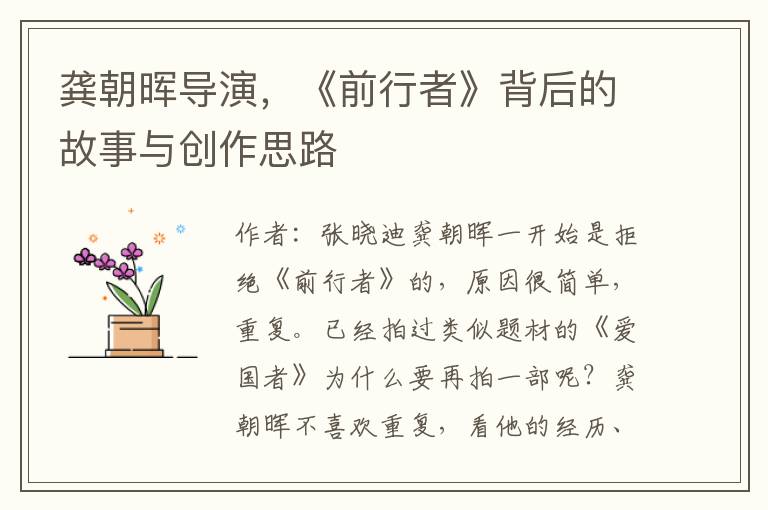
作者:张晓迪
龚朝晖一开始是拒绝《前行者》的,原因很简单,重复。已经拍过类似题材的《爱国者》为什么要再拍一部呢?
龚朝晖不喜欢重复,看他的经历、爱好就知道,上天拍过山,下海拍过鱼,是国家D级滑翔伞运动员,少年时在陶瓷厂给瓶子画过画,在万千考生中脱颖而出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给不少影视剧创作过音乐作品,又是久经沙场的职业导演。所以在他的镜头里,要那么多重复干嘛?
2019年8月,龚朝晖接触到《前行者》这个项目时正在加拿大拍另外一部戏,随后在从加拿大转战美国,又从美国回到国内的长途飞机上看了《前行者》早期的剧本,当时这个项目还叫《党小组》,他回忆说,“问题还是挺多的吧,当然也有很多亮点打动我,题材并不是我选择的标准,有趣的故事,有趣的灵魂才是。”
不久后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再后来整个湖北开始启动封锁防御,全球面临考验,龚朝晖被困在湖北老家,这恰好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好好思考《前行者》。
拍《前行者》是身心重启的过程
“一个民族的崛起,一定会有一群先驱”这是写在《前行者》海报上的一句话,该剧的片头从一群背影开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有那么一群人,在坍塌破碎中前进,向死而生,他们的离去给新世界带来的恰是光明。
关于这部戏的创作,龚朝晖有很多感受来源于他的父亲,父亲是老革命,封闭在湖北的日子爷俩待的时间比较大,谈得很多,看得也很多。“老爷子九十多岁了,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他还戴着建国70周年的勋章到街上去看,自发的想看看哪儿有什么问题。”或许帮不上什么忙,但还是想尽份心、尽点力,这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很质朴的想法。龚朝晖说,“我在拍《前行者》的时候很多方面借鉴了他的故事,甚至包括他的兄弟、战友和上级,先辈的故事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养分。”
经过两个多月的战疫,湖北解封后龚朝晖迫不及待出去“透透气”,他自驾一路向西直奔西藏,一方面是寻找创作灵感,飞驰在路上好好梳理一下思路;另一方面因为自己是佛教徒,希望此行为《前行者》项目祈福。
龚朝晖把此行定义为身心重启的旅程,回来之后带着思考成果立刻投入剧本研讨创作,此时《前行者》制片人董俊、编剧郎雪枫等主创均已就位,摄影指导于小忱还隔离在加拿大,就通过线上沟通的方式开展工作。龚朝晖在画面呈现上定下使用“伦勃朗光”的基调,在微信上和于小忱把片子的光线、设备,甚至使用到的镜头,一种英国五十年代老式的镜头都敲定好了。
伦勃朗光使人物面孔像一幅画,可以呈现微妙细腻的神情,《燃烧女子的肖像》《银翼杀手》都是使用此光的经典作品。英式老镜头的感光性不强,成像四周会比较暗,同样使得画面有柔雾感,并不锐利。
用这种细腻的方式拍一部谍战片,也太冒险了吧?
龚朝晖却坚定地说,“好处是它的代入感很强,这种冷峻中带着温暖的色调,会很快让观众沉浸在我们所营造的氛围当中,把上海当时的黑暗和对光明的渴望对应起来,这是最契合主题的表达。”接着他又换上笑脸,“导演嘛,总要说点漂亮话。”
其实龚朝晖并没有仅仅把《前行者》当作一部谍战戏来拍,他把它当社会剧,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汇聚着形形色色的人,背景、目的各不相同,外表歌舞升平,内里暗潮汹涌。
龚朝晖就是要通过光影塑造拍出人物这种外在的波澜不惊、内心的波涛汹涌。
不断努力创新是龚朝晖的坚持,他总说自己不属于特别有天分、有才华的导演,那就多下点功夫,多从不同途径找灵感、找方法。“我知道我也并没有跳出去,电影发明以来镜头仍然是推拉摇移,我只是希望我们不论从画面还是声音能区别于惯常看到的电视剧,不想总用流行的拍法,我们想不一样。不是为了不一样而不一样,是希望这个故事有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燃烧的剧组的经费
没钱,真没钱!
接触过剧组的人都知道,剧组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就是一进去所有人就自发有一种秩序,特别有责任感,因为大家清楚剧组的每样东西,消耗的每一分钟都能听见经费呼呼燃烧的声音。“钱少、活多、时间紧”是大多影视创作者的心声。
《前行者》的经费也相当紧张,龚朝晖更知道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他不仅是成熟的导演,还有制片人、编剧、演员的经验,对整个生产流程都非常熟悉,这对一个项目来说可谓是宝贵的财富。比如,明明需要80个群演的街上他知道如何腾挪转移只用15个人,还能画面在镜头前产生应有效果。
剧中需要拍法国巴黎的外景,一受疫情影响,二没钱,怎么拍?剧组就找来地图按比例微缩置景和做后期。在前期筹备中把埃菲尔铁塔的位置、巴黎圣母院的位置、周围建筑的位置、摄影机的视角甚至是不同时间、角度的光线全都计算到位,做足充分准备工作,后期呈现出来的效果做到了跟实拍差别不大,几乎能以假乱真。
“这个不是为别人做的,是为我们自己做,我们觉得就要这么做才行。它即呈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又没有浪费东西,节省了很大的试错成本,我们真的是没有钱。”
一边是资金有限,一边又不要墨守成规,这考验的不仅仅是创作艺术,还得靠成熟的团队配合和恰当的资源调配。
就在资金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龚朝晖还做了一件看似费劲不讨好的事,给《前行者》配上电影大片里才会用到的杜比环绕立体音。
导演 龚朝晖
要知道当下国人追剧主要途径是电视、pad和手机,这么高的配置在这样的终端设备上能有什么效果?有这个必要吗?
龚朝晖说,“有!”
作为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龚朝晖做什么事都挺追求极致,常常在专业后期机房做完片子,再从其他设备上一听,不免叹息。
早在2014年,中国首部成熟运用杜比5.1环绕立体声技术的电视剧,就是龚朝晖做的。这次他想再升级挑战一把,当然是建立在不过多增加成本的基础上。
《前行者》声音监制娄炜、录音指导孟健就承担起了这个重任,他们和龚朝晖合作多次,彼此了解有默契,关键是,龚朝晖又笑说,“他们自己就有棚,费用方面好商量。”
导演 龚朝晖
制作过程中他们反复在普通电视、苹果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上测试、调整,考虑观众在不同场景下看剧的问题,居家、地铁上,外放还是带耳机都试了又试,一遍一遍调整。
这么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可能就是,如果始终没人这么做,国剧的工业标准无法和国际接轨。
拍剧也不要放弃用镜头叙事
俗话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因为在一般理解中,电影是一门视听语言艺术,是用镜头来叙事的,而电视剧则是大众艺术,是用人物对话来推进剧情发展。
龚朝晖当然不同意这种说话,即使拍剧他也始终坚持用镜头向观众传递信息。在他看来电影的本体也不是导演,电影的本体依然是镜头。没有机会拍电影,就把电视剧像电影一样拍。龚朝晖理解的现代电影是文学、戏剧、表演、音乐、美术等等综合一起产生化学反应以后的综合体。
因此《前行者》的片头就极具影像冲击力,没有一部影视作品一上来就给观众看一个又一个背影,龚朝晖还是坚持这么做。
有天拍完巡捕房的戏,正好张鲁一、聂远、王聪、赵阳几个人都在,大家在走廊里来回走,那个走廊又可以布光,龚朝晖立刻想,拍他们的背影,而且一定要用这个背影版做电视剧的片头。“这就是走向坍塌的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义无反顾。这种心无旁骛的状态让你感受到这帮人在一块一定能把事儿干成,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展现,我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这样的。”
拍摄过程中,为了更好的实现构想的视觉风格,营造真实生动的社会质感,龚朝晖还做了三件事,第一把所有内景拍摄中呈现的普通玻璃换成毛玻璃,因为在伦勃朗光的营造下,毛玻璃的反光才能最大限度的呈现出他想要的效果。
第二,把制造场景氛围的烟饼换成咖啡豆,点燃咖啡豆那种氤氲缭绕、香气微澜的质感是其他材质难以呈现的。
当然这样一来成本又上去了,用龚朝晖的话说,剧组到后期连换玻璃的钱都快不够了。
第三,关于剧中角色们喝的红酒,有人提出兄弟(双男主人物关系)之间应该喝白酒,但龚朝晖觉得既然我们故事的主场景在法租界,主人公马天目又是从法国留学归来,那就只有喝红酒的氛围才最准确合理。而且关于红酒的品牌,龚朝晖更希望是一款国产的品牌,“其实这里是有一些私心和情怀,因为在那个时代对中国人民来说是艰难的,民族工业一直在逆境中生存发展,但还是有很多民族品牌发展的很好并走向国际,法租界的人会选择好的国产品牌。”最终通过查阅资料和反复的筛选,剧组选择了张裕解百纳作为剧中红酒的品牌,而这款酒的创建年份也和这部剧的开篇时间背景一致——1931年。
虽然龚朝晖只说了三件,但我们都知道他为了这个戏做的事,远不止这些。
追求创新表达、高配置的《前行者》不见得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却是一部值得细品、回味的作品。龚朝晖不免自嘲自己的很多影视剧常常不会大火。但它们就像威士忌,就像蓝调音乐,不是最火爆的东西,但总会有人喜欢。
“我现在为自己拍,更是为欣赏自己作品的观众拍。就像当年学戏剧的时候老师教导说,哪怕台下只有一个观众,我们也要认认真真演完整场戏。 ”龚朝晖说。
对话导演龚朝晖
《影视圈》:你是如何进入影视行业的?
龚朝晖: 我17岁在陶瓷厂工作,上色、烧制这些都参与,那时候有美院的老师来给陶瓷制品绘画,他们一出手就跟我们不一样,我就想上美院,但是考不了。88年考中央戏剧学院,那一届没有导演系就报考表演系,我们一个同学的父亲给我辅导了一下,教我演小品、朗诵,那时候我还不大会说普通话,就到西安一个考区考试,第一轮就给蒙上了。那年我们班全国就招13个人,西安招了2个,我和我们班长郭涛。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正在公园门口摆摊儿,把厂里的一些残次品拿出来便宜卖,我母亲拿着一封信过来说,你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了。我一看,报到的时间马上就截止了,当天离火车开车还有俩钟头,我赶快回去打包,连滚带爬上了火车。
《影视圈》:为什么又要做导演、制片人、编剧,还做过音乐,是因为单纯的演员无法满足表达欲吗?
龚朝晖: 第一次做长篇电视剧的编剧到现在也快二十年了,这个说话也快20年了,03年非典的时候,模仿一部美剧开始试着写剧本,后来在各个项目当中渗透到了各个部门,就慢慢做了编剧、导演、制片人。
做音乐确实是喜欢,一开始是给朋友做,朋友说没什么钱,我说那就好办了,我不要钱,你给我干我就很高兴了。然后拍戏的时候也会找机会跟导演说,我还会写曲儿,你要不要听一听?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型广播剧、央视《东方时空》还有两年的春节特别节目都用过我创作的音乐作品。这些其实不值一提,但这些经历都让我对声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都会作用于我做导演的创作当中。
《影视圈》:现在的观众看的东西很多,甚至培养出了很强的思维逻辑,这对创作谍战片来说是不是提出了一个更大的要求?
龚朝晖: 确实是。实际上我们在拍《前行者》之前有一个东西是确定好的,就是要用现实主义的质感来讲故事。什么叫现实主义?就是不要飞,尽可能所有的事都能用生活逻辑、现实逻辑能讲通。当然我们仍然有没讲通的地方,拍摄过程中没想到更好的方式,一播出突然想通了,这就是我这种天分不够的创作者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影视圈》:经常能这么客观理性的来看待自己的作品吗?很多导演可能不愿意在这个阶段面对这样的问题。
龚朝晖 :拍戏的时候对导演创作是感性和理性交融的事儿,比如一个电视剧可能就拍100多天,没有时间慢慢拍,都会有遗憾。《前行者》里马天目跳楼那场戏,我们开机前就设计好了,所有摄影、美术、演员全沟通好了,哪知道没有考虑到景区的电线里面夹杂着真的高压线,等处理好电线,天光没了。这是这部剧最大的一个遗憾。不夸张的说,看到播出的版本,我恨不得把它再重拍一遍。
但还是不会拍同样的戏,经常有人找我,我会问你确定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吗?经常把人吓跑了。他们可能觉得找最大公约数,看所谓大数据有安全感。从音乐到绘画到一切艺术,大家都是在求不同,而不是求相同。
《影视圈》:《前行者》现在的成绩达到创作之初的预想了吗?
龚朝晖: 从创作层面上讲,我的主创团队和演员为这部剧加了分。但我的剧好像一直没有大火。《前行者》随着播出,越往后大家评价越好,这是一个好现象,也是我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