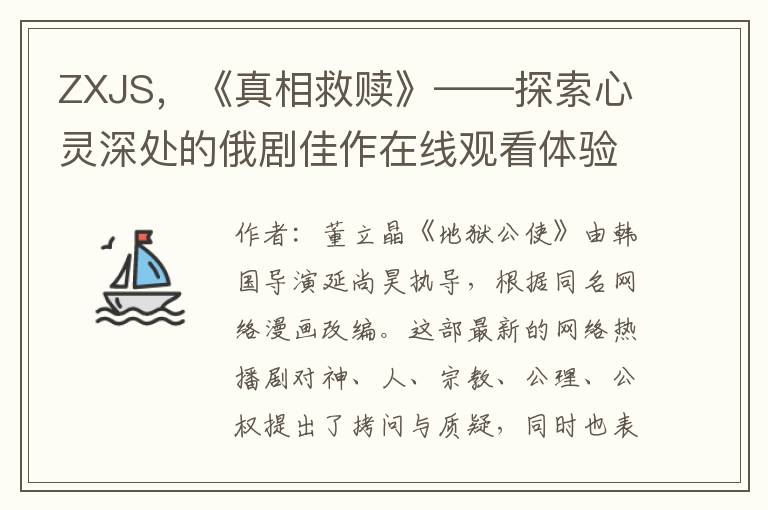
作者:董立晶
《地狱公使》由韩国导演延尚昊执导,根据同名网络漫画改编。这部最新的网络热播剧对神、人、宗教、公理、公权提出了拷问与质疑,同时也表达了信息社会中人该如何自居的思考与反诘。该剧有非常明显的分水岭,前三集为神对人的惩戒,后三集为人对神的反抗,而在构建这两部分时,导演力图处处为续集“留白”,无形中造成了叙事的撕裂和逻辑的难以自洽。但这些并不能遮盖延尚昊导演在剧中所要表现的自省和保留的温存,同时在剧中对“看客”“救救孩子”和“觉醒者”的描摹。
在前半部中,神的宣告和预示,都是针对一些有“劣迹”的人,而新**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大肆宣扬惩戒的正义性,以期获得公众的认可和追随。在剧情一开始就出现了“地狱公使”惩戒罪人的“奇观”,如果说这一事件仅仅是公众的偶遇,那么对于朴静子死亡的直播,则无疑成为新**树立威权的公祭。吊诡的是他们跪拜的并非神本身,而是错愕惊恐的律师闵惠珍,这一镜头已经预示了闵惠珍必将成为新**的“敲钟人”。新**为寻找能够合理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大肆渲染被处刑者的罪行,直播处刑过程,以增加其威望和震慑力。但从所惩处的人所犯罪行来说,未婚生育、公款私用、赌博,这些都“罪不至死”,而作为杀害熙庭母亲的凶手,却逍遥法外,须靠人力通过“非法”途径解决。这样的矛盾和分裂,自新**诞生伊始就存在,也必将因此导致其最终的坍塌。如果说新**是愚弄民众的发令人,箭簇群体无疑成为施刑的屠刀和刽子手,在狂热的躁动下支配着无魂的躯体。警察与法律本应是平民和公共秩序较好的护卫者,但新**的首任议长郑晋守对警察陈京勋的“贿赂”却让警察对新**缄默不语,并且在众多公权部门鱼龙混珠,致使新**的势力急速壮大和膨胀。
作为被选为神谕宣誓对象的被执行者和普通民众,是没有反抗力的,只能被动地接受。如今我们置身网络社会,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你未杀伯仁,伯仁却因你而死”的悲剧。我们生活在密闭的铁屋之中,手握一把无形短剑,不知是刺向他人,还是朝向自己,亦或在些许的罅隙中苟延。无论是剧情一开始的“路人”淡定拍摄死亡的过程,还是朴静子的直播,还有那些戴面具的看客,人们的冷血、漠然已经到了无以附加之地,根本不是在看对同类的斩杀,而是参加狄俄倪索斯酒神的狂欢,是对他者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公然的祭祀。朴静子被直播处刑之所,就是一个舞台,看似孤独的舞者,观者众多,在场的警察、律师、媒体,戴面具的资助者,台下的一众看客,不在场的镜头背后的操纵者和荧屏前的观众,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而此时的朴静子不再孤单,俨然成为一位领舞者。舞台化的表演,“看”与“被看”产生了移置,模糊了界限,人人皆是“看客”,同时也都成为“被看”的客体与风景。没有人质疑新**的合理性和神谕的公正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二者的“规”与“矩”在何方,选择与执行的标准又是什么?沉默螺旋的漩涡在不断地扩大。
接下来的剧情有了反转。新**为了维持自己的公信力,需不停地直播被宣告者及家人的忏悔和死亡执行过程,对于人本身的定义已经完全丧失,毫无任何隐私可言,这些都是新**最终跌落神坛的铺垫。而铸就这些罪恶的恰恰是人类自己,我们亲手编织了这样的罗网。
作为觉醒者的代表——律师闵惠珍,出于对自己曾经签下朴静子直播合同的救赎,亦在自己死而后生之余受到揭露新**的责任的驱使,成立了苏涂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将被处刑者或被处刑者的家人。苏涂意指神道色彩的特殊区域,诸逃亡者至其中即可得到庇护,“以彼之道,还彼之身”。但这个苏涂组织无力反抗神谕,只能反抗新**,避免被处刑者公开处刑牵连家人,也希望找到一个机会能够揭开新**的真面目。新**利用超自然力或者称为神谕选择被处刑者而树立权威和公信,随着裴英宰、宋昭贤新生儿的被宣告处刑,成为新**和苏涂组织较量的关键。闵惠珍接受了众人“朝拜”,便肩负起了扯下新**“遮羞布”的重担,保护被神谕者及其家人的隐私,让世人看到新**的真面目。当三个“公使”杀死了新生儿的父母,新生儿发出的那声啼哭,成为对新**致命的一击,预示着新**的坍塌和神谕的终结。
但是新**为何跌落神坛?“地狱公使”谕旨的规则又在哪里?普通大众到底会走向何方?最后复醒的朴静子是下一个恶魔还是天使?那些被处刑的鬼魅该在地狱中如何自处?这都是剧中留下的伏笔和悬念。“一粒沙中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元宇宙的建立,幽灵与肉体、身心异构、身心合体,在这样的虚拟与现实中,又会幻化出怎样的世界与人类?《地狱公使》所表达的,是韩国的特例,还是世界的共性,值得我们当下人仔细思考。
正如电影《沙丘》的最后一句台词“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这仅仅是开始)”。
(作者董立晶系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管理博士)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