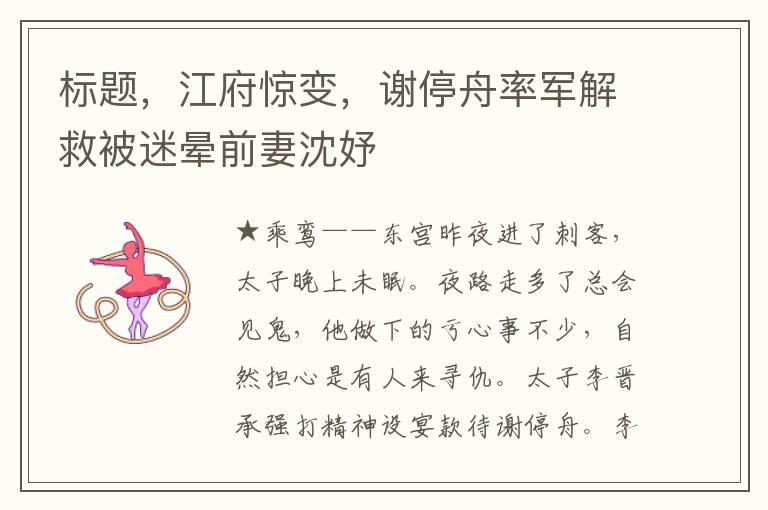
★乘鸾
——
东宫昨夜进了刺客,太子一夜未眠。
夜路走多了总会见鬼,他做下的亏心事不少,自然担心是有人来寻仇。
太子李晋承强打精神设宴款待谢停舟。
李晋承知道谢停舟与李霁风交好,但李霁风就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对他毫无威胁。
北临势大,若是谢停舟能为他所用,那将是一股强大的助力。
日头高照,窗外的树影在地上落成了圆。
谢停舟起身告辞,推辞了李晋承留他用饭的好意,出了东宫,兮风立刻跟上来。
“宫里没找到人,但是有一个疑点。”
谢停舟:“说。”
兮风道:“早晨一个阉人在东宫外对一名宫女动手动脚,被四皇子和江侍郎撞见,四皇子把人送给了江侍郎。”
“江寂要了吗?”
若是没要,那就只是个无关紧要的插曲,若是江敛之要了,那就说明……
谢停舟还没想完,兮风就道:“要了,说起来了还是江侍郎自己开口要的人。”
谢停舟脚下步子乱了。
出宫时,兮风卸了马车。
谢停舟翻身上马,直接策马回了王府,进门就问时雨回来了没有。
王府各方有好几道门,便是回来了,也不知她从哪个门进,下人确认了一遍才来回他,说时雨根本没回来。
谢停舟的心沉了下去,在回来的路上他还想过,她功夫好,只要出了宫定能顺利回来。
若是没回来只有两个原因,不是被囚便是她自愿跟随江敛之回去。
这两种可能不论哪一种,都是谢停舟无法接受的。
谢停舟冷声道:“你即刻调人,把江府给我团团围住,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来。”
“去江府。”他下颌紧绷了几许,“要人。”
说罢再次翻身上了马。
兮风大骇,上前几步劝说:“江府是首辅江元青的府邸,我们如今这样直接上门去要人,实在不妥。”
谢停舟哪管什么妥不妥,调转马头,兮风赶忙上前一把攥住缰绳。
谢停舟勒马,“让开!”
兮风拦在前面稳若泰山,“殿下三思,为了一个近卫大张旗鼓的围了江府,这事这么闹恐怕得闹到圣上跟前去。”
忠伯听说前院闹起来,急匆匆赶来,一听怎么回事,比谢停舟还急。
“那可不行,必须得接她回来,咱们上江府去,翻它个底朝天。”
兮风头疼,原以为忠伯能来劝说劝说,结果来了个拱火的。
“您老别跟着掺和了行不行?”
“不行。”忠伯对谢停舟说:“殿下您看呐,咱们今日就闹到江府去,江家不是出了个首辅还出了个侍郎么,我听说江家的旁支也有不少在朝为官,那是家大势大,可咱们北临王府岂是吃素的?”
“咱们这么一闹,陛下肯定会介入,届时一问什么原因,殿下大胆放言便是,直说江侍郎抢了咱们的人,殿下您看如何。”
谢停舟手中的缰绳松了松。
兮风终于松了口气,忠伯还是只老狐狸,这招反其道而行之用得不可谓不精妙。
兮风靠近了说:“是啊殿下,届时时雨夜闯禁宫的事恐怕也捂不住了。”
谢停舟沉了口气。
他在“心爱”二字下乱了分寸,只要想到她在江敛之手里,便什么也顾不得了。
兮风见他有所缓和,趁机劝说:“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
他谢停舟偏不吃这套。
把沈妤留在江敛之身边,他一刻也不放心。
若连自己心爱的人都接不回来,他这个世子也白当了。
“去调人。”他平静道:“把大黄也带上。”
兮风心一沉,看来是劝不住了。
谢停舟忽然侧头道:“你们忘了? 盛京的人只知我这几年在北临是个彻头彻尾的纨绔,还没真正见识过,今日就让他们瞧一瞧,何为真正的纨绔。”
兮风和忠伯还没反应过来,谢停舟已扬鞭一挥,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
他抬手打了个呼哨,回应他的是一声鹰隼的清唳,一只海东青呼啸着振翅跟了上去。
兮风急得头大。
忠伯却望着谢停舟的背影笑了起来,“这才是咱们北临的雄鹰,盛京的城墙,哪困得住他呀。”
……
江府。
江敛之的院子紧闭院门。
下人们行走间放轻了声音,因为少爷抱着人回来时,脸色十分难看。
还是从前的院子,她住了三年的院子。
江敛之把沈妤放在床上,盯着她的脸,手颤抖着抚上去,还没碰到却停住。
她说她不知他的一往情深从何而起,该从何处说起呢?
或许是上千个日日夜夜的相伴吧,他终究是不知不觉将自己的心送了出去。
可是却阴错阳差地生生错过了。
有水滴落在被面上,洇开了几块湿漉漉的点子。
江敛之握住她的手,喃喃道:“前世欠你的,我加倍还你,好不好?阿妤。”
院子静了一个时辰,院外突然传来一阵拍门声。
高进去看过敲门的人,听了片刻面色一凛,又匆匆赶回来。
“公子,出事了。”
江敛之侧头问:“什么事?”
高进在外头说:“北临世子谢停舟带着人把咱们府给围了,老太爷在养病没敢惊动,现在夫人和老爷在前厅接人。”
江敛之万万没想到谢停舟真敢直接带兵上门来要人。
他原想谢停舟应当对江家有所忌惮,要人只会在暗地里,不会放到明面上来。
谢停舟如今将事情闹得这样大,就不怕把沈妤置于险境吗?
江敛之掖好被角,又放下了帘子,走出房间吩咐道:“派人守好,别让任何人进去,否则提头来见。”
江敛之急匆匆来到前厅,江夫人和江老爷对着上位那尊菩萨正一筹莫展。
见江敛之跨进门,江夫人急忙上前,“敛……”
一声名字还没喊完,江夫人就注意到了他脖子上的血迹,随即大惊失色,“你脖子怎么流血了?”
江敛之并未发觉异常,抬手摸了摸脖子,颈间有些许刺痛。
应当是在马车上沈妤用匕首割破的,他当时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所以没发现。
看来她对他一丝情意也没有,真下得去手。
“没事,不小心碰的。”江敛之看向上座的谢停舟,“不知世子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谢停舟扫了他脖颈一眼,出了不少血,看样子是利器所伤,应该是沈妤和他动过手,却没能走掉。
只是着急寻人,便直接到:“江侍郎这样就没意思了,我来做什么,你不是最清楚不过吗?”
江敛之道:“不清楚,还请世子明示。”
谢停舟既然豁出去了上门要人,说明沈妤在他心里很重要,沈妤是他上午才从宫里接回来的,他赌谢停舟不敢直言。
谢停舟转了转手上的扳指,“我来要人。”
江敛之脸色一变,谢停舟已起身朝他走来。
“前些日子我在醉云楼得了个可心的小倌,听说被江侍郎带回了府上,若是寻常人也就罢了,送你便是。”
谢停舟停在江敛之面前,“可不巧,那小倌是我的心头好,偏巧又付过银子赎了身,不过是寄养在醉云楼而已,江大人夺人所爱 ,不好吧。”
这种情况在京中并不少见,包养个妓子或小倌不好带回府,便寄养在青楼楚冠,谁出钱是谁的人,旁的人不让碰。
江老爷一听,忙上前劝说道:“世子殿下,这中间恐怕有误会,犬子我最了解不过,他不好男色。”
“是吗?”谢停舟半笑不笑地扫了江老爷一眼,随即看向江敛之说:“既不好男色,那便把人还我。”
江敛之低估他了,没想到谢停舟会用这么一招。
谢停舟风评也就那样,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府上没有世子口中的人,恐怕消息有误,世子还是上别处找吧。”
谢停舟垂下手,“来都来了,哪有空着手回去的道理,我得亲自看看才知道。”
他往前迈了一步,江敛之错身拦在他面前,沉声说:“这里是江府,不是你的北临王府。”
谢停舟眸中含着刀,他微微倾身,在江敛之耳边道:“若是我的北临王府,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里同我说话吗?”
他直起身,看江敛之的眼神如同在看一堆垃圾。
江敛之的肩猛的被撞了一下,谢停舟已大步出了门。
谢停舟仰头望天,白羽从空中俯冲下来,落在他肩上,只停留了须臾,又振翅起飞,在空中接连发出了两声尖唳。
果然在府里。
谢停舟抬脚就走。
江敛之厉声道:“拦住他。”
府上家丁立刻上前拦住。
唰——
谢停舟的人马按着腰间的刀,拇指已将刀抵出了刀鞘。
寻常家丁哪里是近卫的对手,单在气势上已落了下乘。
江夫人一看这阵仗,急忙上前劝说:“有话好说,你二人同朝为官,何必闹成这个样子呢。”
她面色不虞看向谢停舟,“你虽贵为世子,但这里是江府,就算要搜府,也得拿出文书来。”
“谁说我要搜府了?我找人。”
谢停舟回首,意有所指,“不是你的,占着也没意思,你何必呢。”
江敛之道:“不是我的,难道就是你的么?”
“那不如叫她出来问一问,看她自己说她是谁的人。”
两人一来一回,除了兮风和近卫,其他人一个也听不懂。
江敛之沉声道:“今日若让你搜了府,我江家颜面何存。”
谢停舟说:“我说了我不搜府,我只在你院中找人,如果没有找到我要找的人,本世子在京中大摆三日宴席,给江府赔罪,如何?”
江老爷已憋了一肚子气,江家最没出息的就是他自己,奈何他生了个最有出息的儿子。
他扬声道:“那便让他搜!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搜得出来!”
江敛之握紧了拳头,并不应声。
江夫人见状,心道不好,“敛之,你,你到底有没有……”
江夫人没把话说下去,因为她已经从江敛之的脸上得到了答案。
江敛之默了半晌,对谢停舟说:“你说的,只在我院中找人。”
谢停舟心中咯噔了一下,难道江敛之没有把人带回来?
不对,刚才白羽来报信,分明是白羽和大黄已经找到了沈妤,那江敛之又是哪来的胆子敢让他搜。
多思无益,谢停舟抬脚就走,江府小厮在前面带路。
江敛之走在一旁,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院子里一名小厮。
那小厮轻轻点了下头,放慢脚步朝着另一条路走去,避开人,他越走越快。
“铛”的一声,一把长刀插入墙壁,小厮急刹住脚步,那刀正好横在他脖子前,刀身还在不停抖动着。
小厮被定在原地,冷汗唰一下冒出来。
如果他走得再快半步,他如今多半已经身首异处。
谢停舟什么也没说,回给江敛之一个眼神。
还没到地方,便听到一阵狗叫声,伴随着白羽尖利的叫声。
走近一看,几人牵着一张网,大黄被兜在网里直叫唤,白羽灵活,不时疾冲而下或抓或啄,弄得几人手忙脚乱。
“兮风!”谢停舟冷喝一声。
兮风上前,唰的一声,抽刀和还刀入鞘都在瞬息之间,那张网瞬间被砍成了碎片。
大黄甩了甩头,跑过来对着谢停舟汪汪叫了两声,又对着院门狂叫。
兮风一脚踹开了院门,近卫一拥而入。
谢停舟径直走向卧房。
帐帘垂落,隐约看见床榻上躺着一个人影。
谢停舟心跳加速,抓住帐帘轻轻拉开。
床上的人忽然睁开了眼,“啊——你是谁?”
谢停舟怔住,手一松,往后退了一步。
怎么会这样?
床上的人掀开帘子下床,她一身宫女的装扮,看了一眼谢停舟身后的江敛之,娇滴滴喊了一声:“江大人。”
江敛之上前,“世子爷看见了,我房中只此一人,我到现在也不知世子在找谁,这是四皇子赏赐的宫女,世子若是喜欢,送你也行。”
卧房被翻了个遍,连柜子也没有放过,还是没找到人。
谢停舟踏出房门,江敛之笑了笑,“届时世子设宴,我定会带全家前往。”
走到院中,谢停舟停下脚步,他回头看向那间卧房,他就是有一种直觉,沈妤就在那个房间里,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大黄杵在门口不肯走,冲着谢停舟直叫唤。
谢停舟目色一凝,疾步冲了回去。
江敛之脸色一变,手中拳头攥紧。
“怎么办?”高进低声问。
江敛之:“他找不……”
后面的话卡在了喉咙,谢停舟已经站在门口,怀里的人被披风罩得严严实实,连一根手指头都没露出来。
“江侍郎,”谢停舟盯着江敛之,声色俱寒,“今日的账,咱们回头再算。”
不知为何,江敛之下意识地让开了两步,看着人与他擦肩而过。
……
马车轻晃,沈妤人还迷迷糊糊不清醒。
谢停舟让她靠坐在怀里,下巴在她额头上安抚地碰了碰,是克制隐忍的一触即离。
“没事了,安心睡吧。”
沈妤仍旧稍仰着头,不大清明的视线固执地落在他脸上。
她不确定地喊:“谢,停舟。”
低沉而嘶哑的声音响在她耳畔:“嗯,我在。”
半阖的双眸几番挣扎,卷翘的长睫抖动了几回,仍旧在坚持着不睡。
“谢停舟。”她又唤他,仍旧是不放心。
谢停舟知道她意志力素来强大,到现在快要失去意识都还在强迫自己。
他轻轻叹了口气,拥着她往上提了些许,为她找了个更舒适的位置。
低头看她的脸,低声哄道:“睡吧,到家了叫你。”
“好。”她声若蚊蝇。
谢停舟心疼的像是被人割了无数刀,抬手轻轻划过她的眉眼,低下头,将薄唇印在了额间。
看着她渐渐睡沉,谢停舟才缓缓抬头。
“兮风。”
“在。”兮风立刻下马上了马车,犹豫片刻才掀开车帘。
“殿下……”
谢停舟目光越过他看向虚空:“安排一名暗卫从宫里逃脱。”
兮风立刻明白过来,如今宫里在查刺客,若是一直找不到人,恐怕会怀疑到出宫的这些人头上来,届时便能顺藤摸瓜查到时雨身上。
“是,我这就去安排。”
谢停舟昨夜便一夜未眠,白日都是强打起精神,紧绷的神经一旦松懈下来,困意便铺天盖地来袭。
回府后靠在榻上,怀里抱着沈妤,迷迷糊糊地就睡了过去。
更漏声不知响了几回,窗户上映着婆娑的树影。
沈妤迷迷糊糊睁开眼。
榻边摆了张椅子,谢停舟坐在里头,正垂眸盯着她的脸。
“醒了?”
沈妤半是清醒半是懵懂地睁着眼,缓缓点了点头,一句话也不想说。
她这一觉睡得极好,似乎很久未曾睡过这么踏实的一觉了,她翻了个身,懒懒地趴在榻上,不怎么想动。
“什么时辰了?”
谢停舟倾身,替她拉好下滑的被子,“刚过丑时。”
他在未时接她回来,陪她睡了两个时辰便醒了,她却一直睡到了半夜。
再过一个时辰,天就要亮了。
沈妤抬眼,她在马车里闭眼时,并非一下就昏睡过去,那抚在脸上的手指,还有额头上柔软的触碰她都知道。
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谢停舟,觉得那像是一场梦,又比梦里更加清晰而旖旎。
谢停舟突然问:“看着我做什么?”
沈妤当即闭上眼,“那不看了。”
谢停舟倾身靠近,勾着她的下颌,“沈妤,看着我。”
沈妤听到他轻浅的呼吸,整个人如同被笼在一阵淡淡的松木香里,分不清是来自他的床榻,还是来自他身上。
她不敢睁眼,“一会儿让看一会儿不让看,你到底要……”
沈妤怔住了。
额上骤然贴上一片柔软。
这一次比上一次要清晰太多。
沈妤睁开眼,只能看见他的下颌,鼻尖离他的喉结不到三寸的距离。
他的喉结在滚动,近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
松木香的味道更浓了,似乎比江敛之的迷香还要厉害,让人沉溺其中,连攥着被子的手指都没了力气。
谢停舟缓缓退开,乱了呼吸:“现在,能看我吗?”
沈妤尚未从这一吻中回过神,愣愣地看着他的脸。
“傻了?”谢停舟抓住她的手,掰开她的手捏在掌心。
“傻姑娘。”他低声道:“若有人这么轻薄你,你应该当场给他一巴掌,或是拿刀划开他的脖子,不能由着人这么欺负的。”
掌心微痒,沈妤任由他的拇指抚过那一排被指甲压出的月牙痕,“我,我才不会被人欺负。”
“那为什么不打我?嗯?”谢停舟又问。
他知道她坚韧却又固执,引导着想让她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
沈妤的心乱了,她咬着下唇闭口不言。
来京的路上明明张口就能调戏到谢停舟哑口无言,真到了关键时刻,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谢停舟叹了口气,唯恐逼她太过反倒让她退缩。
他起身走到桌边将半杯冷掉的茶喝掉,手指搭在桌上敲了几下似在思考什么事,转而又另拿杯子倒了杯热的给她。
沈妤拥着被子从床上坐起来,接过茶抿了一口,问:“你又是一夜没睡吗?”
“睡了。”
“怎么睡的?”
谢停舟半笑不笑,看得沈妤心里一阵似一阵地发慌。
“榻上睡的。”
沈妤的心跳乱了一拍,转念又想,进京一路上两个人都不知睡过多少次了,一起睡一觉又有什么,于是定下神来。
“昨夜我打听到一些事。”
谢停舟看着她,“打听到什么?”
那迷香让她昏睡了大半日,她仔细梳理了一遍,说:“我在大理寺时锦衣卫刚好来提人,同绪帝大半夜提葛良吉进宫一定有问题,于是我就跟着囚车进了宫。”
“太冒险了。”谢停舟沉声道。
“我下次注意。”沈妤心虚道。
谢停舟抬眼,“线索可以慢慢查,但不能拿自己去冒险。”
沈妤开口想说话,却又闭上了嘴,面上似羞愤又似恼怒。
半晌,她捶了下床沿,“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谢停舟愣了一下,“我怎么没好好说话了?”
“你就是……”沈妤顿了顿,“谈事就谈事,你讲那么多有的没的干嘛?”
谢停舟怔了片刻,陡然失笑,“好,我好好说。”
沈妤又觉得不对劲了,好说就好好说,偏要用那么宠溺的语气是想干嘛。
“又有问题?”见她表情有异,谢停舟问。
沈妤别开脸,“没有,现在我们好好谈。”
谢停舟唇角笑意不减,觉得她这模样可爱得紧。
“先喝口茶。”
沈妤把杯子里的茶一饮而尽,准备放在旁边的小几上时被谢停舟接了去。
谢停舟,“说吧。”
沈妤想了想,把在大理寺狱中从葛良吉口中得知的消息,还有同绪帝和葛良吉的对话说了一遍,
谢停舟沉吟半晌,“葛良吉给他的子女留下的保命符,一定是对方忌惮的东西,说不定就是能取对方性命的证据。”
沈妤点头,“我也是这么想,后来在宫里,葛良吉说蛀虫里他也占一个,说明他确实与此事有关,但还有其他主谋。同绪帝明显也知道那些人是谁,但是他不想动或者是不敢动。”
谢停舟食指敲着空杯,沈妤见他在思考,不想扰乱他的思绪,安静等着。
过了许久,敲击的手指一停,谢停舟把杯子搁在一旁的矮几上。
“同绪帝最在意的是什么?”
沈妤怔了怔,不确定地说:“应当是……大周的江山吧。”
“没错。”谢停舟道:“燕凉关一役已伤了大周的根基,可在同绪帝眼中,有什么比拔除这些毒瘤更为可怕?”
沈妤想起了同绪帝说的五大恶患,还有他对几名皇子的评价。
宦官争权已解,奸佞想除却不敢除,内有党争……
她脑中灵光一闪,喃喃道:“骨肉相残。”
谢停舟道:“能排在奸佞之上的,唯有骨肉相残了,他明显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几位皇子里堪当大任的不多。”
“我想起来了。”沈妤说:“葛良吉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或许一开始我的方向就错了,他们杀我爹的原因不是功高盖主也不是仇杀,而是为了自保。”
皇子,继位,争权,自保,沈妤将这些词一个一个联系起来。
皇位之争,胜者黄袍加身,败者粉身碎骨。
沈仲安拥兵十万,定是诸皇子争相拉拢的对象。
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称作自保呢?
那便是知道沈仲安已经成了对方登上皇位的一大阻力,不得不除。
沈妤越想越心惊,抓着被子的手都在颤抖。
谢停舟握住她的手,“沈妤,看着我。”
沈妤抬眸看着谢停舟,眼中冒出了血丝,“他们太丧心病狂了,为了一个皇位,他们……”
谢停舟安抚道:“皇家本就是这样,多少皇子死于皇位之争,连自己的父母和亲兄弟都能杀,又有谁是不能舍弃的呢?”
他声音渐渐低了,忽然苦笑了一下,“别说皇家,王侯将相也是一样。”
沈妤注意到他这句话中的失落,定定看着他的脸。
谢停舟半边脸隐在烛光里,侧脸冷硬,眉间渐渐涌上了阴郁。
他盯着虚空的地方看了半晌,目光一转正好撞上沈妤担忧的脸。
那激荡在胸中的阴郁,因她这一眼,悄声无息地退了下去。
“怎么?”他问。
沈妤默了须臾,诚实地点了点头,“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过的事?”
“嗯。”谢停舟说:“但是你这么看着我,我忽然就不难过了。”
他的声音很低很沉,又很好听,充满着蛊惑的意味。
谢停舟喉结滚了下,目色深了些,“那你……抱一抱我。”
他眸色很深,却不染半分欲念,强大而温柔的谢停舟,第一次流露出这样类似脆弱的表情。
沈妤心软了,也心疼了。
她缓缓伸手,手指划过他的手臂,然后是肩……
还没来得及拥抱他,她已被他强而有力的双臂箍进了怀里。
外头梆子声密而急,已经是尾更了。
外间点起了灯,屏风半透,谢停舟更衣的影子落在屏风上。
沈妤侧卧在床榻上,盯着屏风上谢停舟的轮廓。
穿好衣服,谢停舟又绕了进来。
沈妤看见了他身上的朝服,坐了起来,“你要去上朝吗?”
谢停舟领了个有名无权的闲职,平日里是不需要上朝的。
谢停舟“嗯”了一声,“昨日葛良吉已被处斩,宫里又出了事,去看看。”
沈妤点头道:“那我回鹿鸣轩去。”
“别急。”谢停舟拦住她,“早上大夫要来给你诊脉,不知道昨日的迷香对你的身体有没有损伤,你再睡会儿,时辰还早,我先走了。”
走到门口时,他回过头,她一身寝衣坐在榻沿,见他回头,冲他笑了笑。
谢停舟心里忽然生出一种感觉,像是寻常夫妻,早起的丈夫和送别的妻子。
出门时她送他,归家时她等他。
若每日都是这样,这盛京,似乎也不那么无趣了。
……
沈妤睡了一日,根本就睡不着了,榻上的味道让她安心,躺到辰时,她才起床洗漱。
大夫来诊过脉,说她脉象正常,那迷香对人无害,有安神的作用,只是剂量用得重了一点。
丫鬟进来摆早膳,沈妤吃着,抬眼时看见长留在门口探了个头进来。
“杵那干嘛?进来呀。”
长留背着手进来,看看沈妤又探头看了看里间,疑惑道:“你昨夜,是和咱们殿下一道睡的吗?”
沈妤正喝着粥,被他这么一问,一口粥险些喷出来。
好不容易憋回去,呛得她直咳嗽。
长留吓了一跳,赶忙给倒了杯水,“你可别害我,殿下让我别吵你,你咳死了殿下要罚我。”
“岂止是罚你。”忠伯走进来,一边把东西放下,说:“殿下得扒了你的皮。”
长留摸了摸自己的脖子,上下打量着沈妤,“你到底给殿下和爷爷灌了什么迷魂汤,从前他们可是最疼我的。”
沈妤干笑道:“你如今依然是。”
忠伯揭开盖子,把一盅红枣燕窝摆在沈妤面前,“趁热喝了,往后每日都得喝一盅,滋阴补肾,于身体有好处。”
沈妤听到那句滋阴补肾就头大,幸亏长留没听出来,赶忙说:“不用了吧。”
“用的,赶紧喝。”
长留探头看了看,他爱吃甜食,红枣燕窝甜腻的香气让他直咽口水,“于身体有好处怎么不给我吃?”
“你小孩子家家的吃什么吃!”
长留指了指沈妤,“他。”又指向自己,“比我,大了才不到两岁呢,他就不是小孩子家家了?”
“那就再长两年,等你比她大了再说吧。”忠伯敷衍了句,又摆起笑脸看向沈妤,“怎么样,味道如何?若是不喜欢我让厨房调整配方。”
长留唰一下,背过身,坐在椅子上生起闷气来。
“挺好,挺好的。”沈妤干笑道。
“那就好。”忠伯说完,偷瞄了沈妤一眼,忽然沉了脸叹了口气。
沈妤:“忠伯有事吗?”
忠伯严肃道:“今日殿下进宫,也不知是吉是凶。”
沈妤放下勺子,“发生了什么?”
“殿下不是不让说吗?”长留转过身问。
“你闭嘴。”忠伯往长留嘴里塞了块点心,转而对沈妤肃然道:“你有所不知,殿下昨日为了救你回来,带兵围了江府,江府是什么地方?那可是四大世家之首,祖上曾出过一位太傅,两位首辅,三位尚书,其他官职数不胜数啊。”
忠伯尽量往严重了说。
沈妤暗自心惊,她只知谢停舟救她回来,却忘了问他用了什么方式,没想到竟闹得这样大。
忠伯道:“咱们家殿下哪儿都好,就是喜欢自苦,报喜不报忧。”
沈妤吃不下了,怪不得一大早谢停舟就要进宫去。
“会有事吗?”
“这就不知道了。”忠伯说:“不过你若是去宫门外等着,肯定能第一时间知道消息。”
长留刚想开口,却见忠伯对他眨了眨眼。
卯时上朝。
谢停舟刚踏入承天门,李霁风便急匆匆跑来。
他压低了声音说:“你如今正在风口浪尖上,怎么竟跑到上朝来了,你知道昨日闹得有多大吗?”
“知道。”谢停舟道:“所以我来了。”
李霁风原想着把他给劝回去,谁知人家是自己乐意往枪口上撞。
他跺了跺脚,跟着谢停舟往宣辉殿走,“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江家在朝堂的势力盘根错节,一会儿殿上若是有人对你发难,我也好帮个腔,你是我兄弟,不能叫人欺负了去啊。”
谢停舟暼他一眼,“江寂抢了我的人。”
“还真抢了你的小倌?”
李霁风也听说了怎么回事,但他觉得那不是谢停舟的作风,要么就是那小倌天姿绝色,连谢停舟和江寂这样的都无法抵抗。
殿外百官俱在,两人一到,其中一群人便看了过来。
“你看。”李霁风低声说:“这些肯定是他们的党羽。”
谢停舟笑了笑,不退反进,走到离江敛之三步的地方停住,“昨日江大人还红光面满,这才一日,怎么憔悴得如此厉害?”
“着你就不懂了吧。”李霁风趁机唱双簧,“小孩都知道哭着要糖吃,何况是大人呢。”
言下之意是说江敛之装腔作势,故意装成这模样来博同情。
站于江敛之身后的大臣憋着满脸怒气不好发作,刚想为江敛之抱不平,江敛之抬手制止。
“世子莫要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谢停舟施施然抖了抖袖子,“那江大人也别觊觎不属于自己的才好。”
李霁风帮腔,“对!别觊觎!”
谢停舟无语,侧头看了他一眼。
李霁风一脸茫然,“你看我干什么?”
谢停舟抬脚就走,低声对李霁风说了句,“一会儿在殿上不管他们如何发难,你不要开口。”
“为什么?”李霁风问。
鸿胪寺静鞭响了三下,百官肃静,“唱”奏之后依次进殿。
昨日葛良吉刚被处斩,估计不少人都松了口气。
奏报之后,一位大臣站了出来,“臣有本启奏。”
来了!
谢停舟回头看了一眼,是右副都御史张怀兴。
同绪帝:“准。”
张怀兴行了礼,开口道:“臣今日弹劾北临世子兼都指挥佥事谢昀,招募私兵,带兵围困首辅大人的府邸,简直罔顾律法,罔顾国体,视纲常于无物,臣请陛下严办。”
谢停舟泰然自若,听得殿中几声“臣附议”,他甚至轻飘飘地笑了下。
“张大人,你说我招募私兵,这罪名从何而来啊?”
张怀兴道:“世子竟还敢狡辩,昨日围困江府的那些人,可是不少人都看见了,你还想抵赖吗?”
“那你数过吗?一共多少?”
张怀兴气愤道:“那么多人,臣怎能一个一个数?”
谢停舟道:“既然没数过,又如何认定我超了规制呢?”
张怀兴说:“按律亲王三十六守卫,二十贴身护卫,世子总不会比亲王规制还高吧?”
“那自然是比不得亲王了。”谢停舟看向同绪帝,“臣进京时,陛下特许臣藩王规制,领三护卫营,按理说昨日所有加起来,也不到一个护卫营的一半吧。”
张怀兴:“这……”
同绪帝颔首,“确有这么回事。”
张怀兴哪会知道同绪帝和北临私下达成的条件,一时下不来台。
“即便如此,那擅自围了首辅大人的府邸又作何解释?”
谢停舟觑了江敛之一眼,“不如你问问江大人怎么回事。”
“銮殿上岂容你推三阻四!”
谢停舟冷冷一笑,“何时又轮得到你来质问本世子?”
左副都御史万睿贤刚准备出列,却见谢停舟不露声色地扫过众人,视线在他身上多停留了片刻。
他瞬间明白过来,背上冒出了薄汗。
幸亏方才他没替谢停舟说话,同绪帝忌惮北临,若同绪帝知道在朝中还有谢停舟的人,又会作何反应?
如今越没人替谢停舟说话,同绪帝就越是放心,反倒不会如何处置。
“江大人。”谢停舟看也没看江敛之,“今日在殿上,不如把事情都说清楚了。”
江敛之被逼出列,“臣与世子小有摩擦。”
谢停舟悠悠道:“这事说起来呢,其实不好放在殿上来说,不过张大人既参了我一本,那还是要说清楚的,我平日流连秦楼楚馆,实不相瞒,有个心爱的小倌。”
此言一出,殿中哗然。
这等不入流的事情,怎能拿到朝堂上来说,简直有失体统。
谢停舟继续道:“说来也巧,连江大人这样洁身自好的人,竟也和臣看上了同一个,偷偷将人掳到了府上,若是寻常的也就罢了,但心爱之人岂能拱手相让。”
“一派胡言!仗着自己是北临世子便诬赖朝廷命官。”
“简直胡扯!江侍郎风霜高洁,岂会行此不轨之事?”
谢停舟看向江敛之,“江大人,如何?”
江敛之握紧了拳头。
如果直言,便会将沈妤搭进去,谢停舟是算准了他不敢,还是说沈妤在他谢停舟心里根本没那么重要?
江敛之提袍跪下,“确有此事,臣有失体统,还望陛下恕罪。”
。
这便是默认了。
方才那些一口一个风霜高洁的已哑口无言。
张怀兴满头大汗,富贵人家的家宅中多少有些见不得光的事,只是他没想到江敛之竟也是这样的人。
今日若不是他当殿弹劾谢停舟,又如何会将江敛之后宅的事公诸于众。
谢停舟笑了笑,“陛下知道我什么德行,我混账惯了,若连找个小倌也不行,那在这盛京待着也忒没意思了。”
盛京没意思,哪里才有意思?
不就是北临么?同绪帝又岂会放虎归山。
说到底,不过是两个世家子弟为了个伎子争风吃醋,拿到朝堂上来说实属不该。
但谢停舟昨日围了江府是事实,若是不给江府一个交代,单是文武百官面前就说不过去。
往后世家子弟争相效仿,今日你带家丁围我,明日我带小厮围你,那不得乱了套了。
同绪帝沉吟片刻,说:“你二人为了个小倌争风吃醋,确实有失体统,便罚谢昀禁足一月吧。”
“一个月啊。”谢停舟叹了口气。
李霁风一听,一个月,那还得了啊,他之前被皇帝禁足半个月都要命了。
他上前一步,“父皇,明明是江侍郎抢夺在先,怎么只罚停舟一个?”
“你闭嘴。”同绪帝沉声道:“户部如今由江寂代为主事,暂不禁足,罚俸三月代之,可有异议?”
“臣领旨。”“臣领旨。”
谢停舟,江敛之二人同声。
“不过……”谢停舟拖长了调子,“陛下,我看江侍郎后院无人,竟沦落到和我一样流连楚馆,实在有损江侍郎高风亮节的形象。江侍郎和我不同,他可是国之栋梁。”
同绪帝听出了谢停舟的言外之音。
江寂已过弱冠,如今还未娶亲,是该把赐婚提上日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