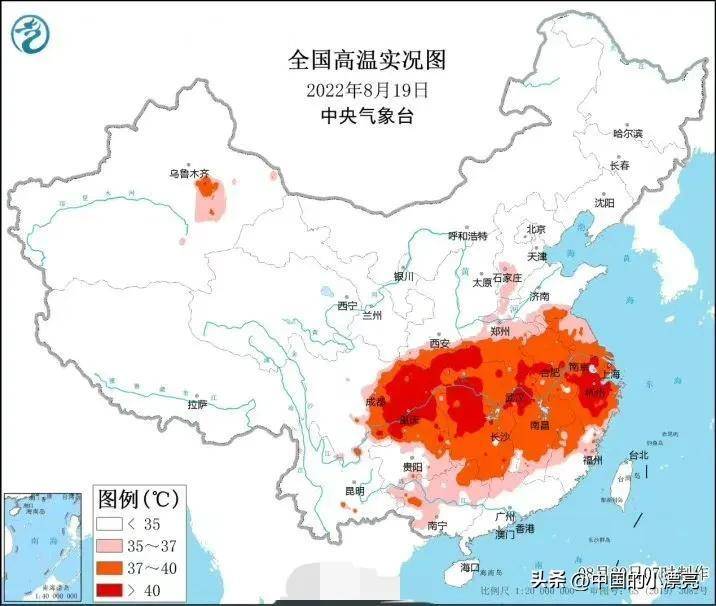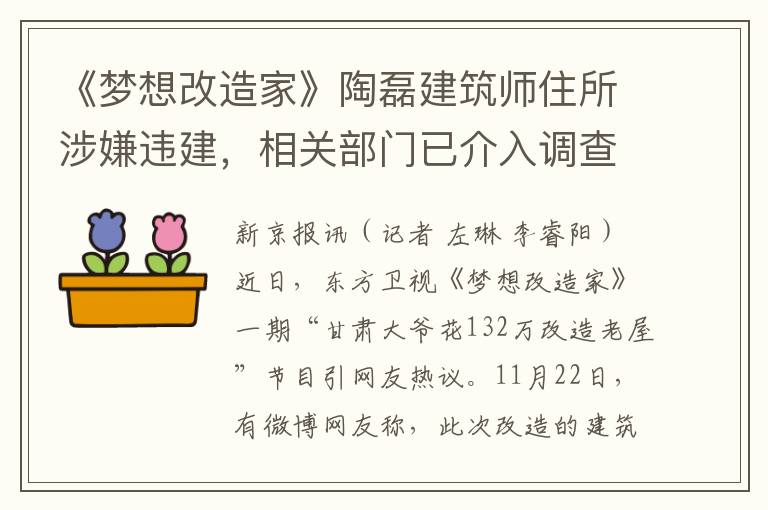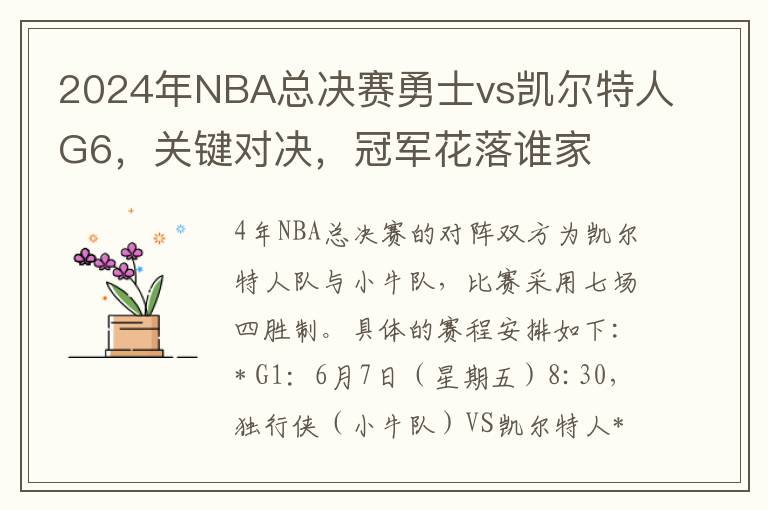本文作者:秋叶飘零
助阿德里安·布洛迪拿下奥斯卡史上最年轻影帝的《钢琴师》,是一部优质佳作,前几年已经看过一次。真实的故事,根据波兰犹太钢琴家席皮尔曼自传改编,导演罗曼.波兰斯基,2002年上映,获得法国恺撒最佳电影大奖。

男主饰演者阿德里安本会弹琴,拍片的几个月中,每天练琴四小时,还要减肥。1.83的个头,减了30公斤,最瘦时仅61公斤,我还以为导演特意找了个细高条儿。
再观,引发思考:生死面前,出众的艺术才华,是否可以成为不言而喻、一致默认的生存优先权?扩展开来,不止艺术,科学家、作家、学者、着名演员等,可为本民族或全人类创造更多科学成果、思想智慧和艺术产品等,其生命价值更高,是社会精英、文化种子、杰出人材。
如此一来,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又当何论?现实中这似乎不是个问题。说说熟悉的事例:抗战时期香港沦陷,东江纵队受党指示,组织大规模“抢救文化人”的活动,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邹韬奋等人,虎口脱险,到了重庆昆明等大后方。
还有北大清华南迁,组建西南**,为了保留和庚续民族文化血脉,在兵荒马乱战火烽飞中。
无可厚非。作为个体,创造的社会物质或精神财富更多更精,对社会和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理应受到尊重和优待,符合“多劳多得”原则。
问题是,赶上子弹不长眼的战乱,他们的生命安全,是否要以别人的风险甚至牺牲来保障?我想,这恐怕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电影中,席皮尔曼一家人将被赶上死亡列车之际,有人一把揪住钢琴家摔到身后,催他快走,冒死救下艺术家。至于其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无能为力。

之后,在犹太隔离区干苦力,有人把单薄瘦削的他,调到仓库当管理员。当他加入地下反抗活动时,有人安排他逃到非隔离区。再往后,东躲西*,朋友们冒险为他提供住处食品、医药治疗。
这个被抓了,转到下一处,都认识和赏识他,千方百计保其安全。最终,所有联系中断,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在废墟中翻找东西充饥,被一个德国军官撞见,却成了救助他的最后一个接力棒。

这是全片最紧张危险的悬念,也是最不可思议的“戏眼”,难以置信地发生了。可信吗?当然,是真事,下面就影片情节和细节分析一下。
朋友安排他躲在德军医院和秘密警察总部对面的楼上,反而是最安全之处——灯下黑。战争临近结束,楼上有爱国勇士狙击反抗,引来德军报复搜查。他在屋顶险些中枪,快速穿过街道,想到对面人去楼空的医院,一列德军经过,伏地装死——尸横遍街。
残垣断壁,饥肠辘辘,找到一个罐头,用力敲打,洒出一地果汁,顺着滚落的罐头,只见一双军靴。一个军官,冷冷地盘问: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住在这里么?你的职业?“我是个钢琴师”。军官似乎长叹一声,推开一扇门:来啊,弹吧。

他摩搓双手,几年没摸琴了,怯生生开头,摸索音阶,试弹,渐入佳境。军官坐下聆听。或许平生最后一次,索性尽兴一把,流畅娴熟,越来越激动、激昂。
酣畅淋漓之后,等候最后时刻。军官又问:犹太人?你躲在这里?带我去看阁楼。有食物吗?(废话)然后开车走了。
之后送来吃的,告之:俄国人正过河,再等两个礼拜就可以了。撤退前,又送来一大包食物,“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感谢上帝吧,他让你活下来的”。战后打算干什么?在电台弹琴。告诉我名字,我会听你演奏的。临走脱下军大衣,递过去。

我注意到一个镜头:军官办公桌上,有张与家人孩子的合影,说明此人爱孩子、重亲情,保留着人之常情,没有异化成六亲不认冷酷无情的战争机器。
他是路过或在办公室听到动静,才发现席皮尔曼的吗?显然不是。钢琴家即使饿得发疯,也不会弄出要命的响动,除非有人跨进这幢破烂的建筑。
军官知道那间房里尚有完好的钢琴,他来过,来干什么?应该是来弹琴!席皮尔曼弹琴时有个路边吉普的镜头,琴声清晰可闻,警卫(或司机)纹丝不动。
长官进去,传出了琴声,如果这是异常情形,大头兵指定会冲进去。只有一点可以解释:这是常态。而且军官的琴艺想来相当可以,乐盲听不出好歹。
血腥的战争持续了几年,但凡不是嗜血狂魔,有点正常人性的,心理神经都受不了,需要精神缓冲和减负,这个军官八成会来调节一下。
他听得出眼前这个叫花子似的犹太佬,弹出的乐音之出类拔萃。席皮尔曼命大、幸运,遇上了知音,(仅限音律)欣赏和珍惜稀世才华。
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和对音乐家的尊重,军官送来食物和关爱,希望钢琴家能活下去,日后能再次聆听难得的艺术享受。不过依片尾推测,成了战俘的他大概率没这耳福。
当然,不排除有另一层考虑:这位高手不是一般的人物,败局已定,给自己尽量铺点儿退路吧。紧要关头,他托人带口信给钢琴家,盼望席皮尔曼前来作证。晚了一步,关押地渺无人影。
打动军官之心的是音乐,音乐可以柔化人的心肠,令其还原为一个比较正常的人。反之,有文化、懂艺术的人,坏不到哪儿去,成立么?No!纳粹党卫军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放着瓦格纳的音乐杀人!知识理性和道德理性完全是两码事,康德在三大批判中,早就论证过了。
忘了在哪本严肃学术期刊上读过一文:战后优待俘虏,音乐会上一个德国军官很是不屑,弹的什么玩意?不服你来!上去叮叮咚咚一通,众皆诚服。战前你是音乐人士?哪里!业余爱好,票友一个。
德国出现了较多的哲学家和音乐家,若论逻辑思维和艺术修养,日耳曼人充分显示出“优等民族”的禀赋和传统。可是,当一种似是而非的民族主义理论甚嚣尘上时,大多数人狂热得毫无理性,对全世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犹太人受害尤烈。

由此,自19世纪末出现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得到血淋淋的实锤。文艺复兴以来日益膨胀的人类的理性自负,只是自欺欺人,实在靠不住。地球上哪种生物会这样大规模地自相残杀?保护本能被所谓理论话语忽悠得不及动物,还好意思扯什么“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雷特之语)
战后,探讨人类疯狂行为之下的文化思考和人性追究,深入到群体潜意识层面,如勒庞的《乌合之众》、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等。如何避免有人利用人性的弱点,造成盲目附合随波逐流的社会无理性势态,从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每个有头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应是每个人严肃思考的问题。
这个情节也说明,人之善恶,不能简单以群体而论。观影时瞄到上方一则弹幕,说军官是又一个辛德勒,未免言过其实。我想起雨果的小说《九三年》,或更贴近。
被包围的侯爵本可逃生,为救几个农奴的孩子被捉;**军司令郭文因其偶现的人性光亮,私下放了敌首;政委在执行枪决郭文的命令时,陷入纠结亦开枪自杀。从大美大丑鲜明对立的《巴黎圣母院》,到最后一部作品中复杂的美丑善恶交织,作家审视人性的复杂多重、深不可测。
自然,能在众声喧哗中保持清醒头脑的,终是少数异类。当席皮尔曼兴奋扑向苏军时,子弹呼啸而来——因为那件军大衣。他大喊“我是波兰人”,当被问及大衣时,只答“我很冷”。说出真相是危险的,有通敌之嫌,确实匪夷所思,若非真事。
六年后,钢琴家在电台弹琴,还是片头肖邦那首夜曲,被炸弹和战争打断的。同一个人,同一个场景,同一首乐曲,似乎一切只是一场噩梦。只是,主人公的眼神变了,深沉而忧郁。失去了亲友,经历了生死,与肖邦的心曲相近,琴声有了凝重的情感色彩。
片头的音乐家
片尾音乐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