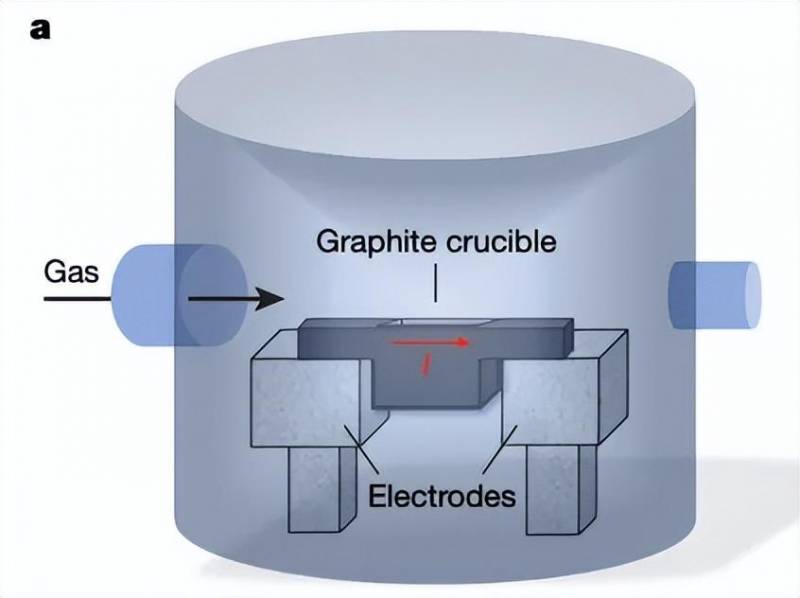莫言评价余华中学gai溜子造型
莫言、余华、苏童是我们熟悉的文学作家,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负责教书育人的“老师”。
在这背后,有一段故事渊源——1988年-1991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鲁迅文学院曾经联合招收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从这个班级里,走出了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
为了赓续这样优秀的历史传统,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国际写作中心又共同设立了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在国内首创“学术导师”和“作家导师”联合培养的双导师制,邀请莫言、余华、苏童等作家来担任博士联合导师,目前已经招收了12名博士研究生。
教育成果如何?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叫做《耘:每当有人醒来》的书籍,收录了来自这12位青年作者的12部中短篇小说。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了一场研讨会,莫言、余华、苏童等悉数到场,聊到他们对自己学生创作作品的看法,也谈到了“青年的写作能力如何养成”的话题。
在这场研究讨会上,莫言提到,好小说确实是改出来的。他对到场的学生说:“无论多么大的才华,像李洱的小说也是才华横溢,但是他也要改,徐则臣也要改,我的更要改。”
余华讲到很多,他特别指出自己对学生作家教育的观点:培养学生不是看现在已经发表了重要作品,而是将来能否在文学上真正取得成绩的作家,“我们不以发表作品来衡量一个作者。”
以下是莫言、余华、苏童在当天研讨会上的讲话,已获授权:

莫言:好小说确实是改出来的
老师们,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的编辑家们,你们的到来使我们的会议有了实质性的内容,我们说一千道一万都没用,只有你们说一句、说两句才真正发挥作用,你们看了这个稿子拍案叫绝,我们在后边如果能看到这个景象会热泪盈眶的。略为夸张一点,反正我会热泪盈眶,苏童会不会我不知道。所以编辑们背后的工作,怎么感谢都不过分。
我们当年也是年轻作者,我们也都是各个刊物的编辑帮扶成长过来的,而且这样的故事我们都重复了无数遍,讲了一遍又一遍,别人听着不厌烦,我们讲着也不厌烦。
当年,我们每发表一篇作品背后都凝聚着编辑老师的汗水,后来当我从《人民文学》编辑部把《红高粱》手稿要回来的时候,我看到编辑标注的痕迹,什么大二号、小二号那些专业的编辑术语,以及他们翻稿纸时候留下的手纹,所以手稿的意义在于除了作家的劳动成果之外,别人的劳动成果。

我应该代替老师们和我们的同学们,对今天到会的各位编辑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本小书《耘》也凝聚着你们的劳动成果,这本书从装帧设计到内容真是好,这本书掀开扉页就感觉才气扑面而来,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三个扑面而来,怎么可能不是一本好书?
当然接下来要感谢我们的作者、我们的同学们,你们的才华、你们的劳动也是我们的光荣。所以当我们写不动的时候,看到像自己孩子一样的同学们在写作,而且出了成绩,内心深处的欣慰确实难以言传,这是非常真诚的,一点都不假,甚至一点都不亚于当年我们自己的作品发表前那样一种兴奋。当然有时候稿子如果被拒绝,心里面也是不太舒服的,一方面稿子为什么我觉得不错别人觉得不行?是我有问题还是别人有问题?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可能双方都有问题,这需要我们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进行调整。
好小说确实是改出来的,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无论多么大的才华,像李洱的小说也是才华横溢,但是他也要改,徐则臣也要改,我的更要改。所以我们找到当年的手稿你会看到改的痕迹,而且编辑老师的意见尤其要参考,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出版的问题,刊发、登载的问题,所以他们综合文学的因素和多方面的因素来做出这样、那样调整的意见。
余华:不以发表作品来衡量一个作者
这本书里有很多作品我没有读过,没有读那么仔细,我只读过几篇,因为我到北师大来算是最后一个。当然最早是莫言在这,然后苏童、江河、西川过来,我是最后一个过来的。
我们对于学生的“发现”,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在发现。我们不是看一部作品的完成度怎么样,有些作品可能从完成度的角度来看的话已经很完整,但是它未必有什么地方吸引你,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个学生的一篇作品,可能中间有几个细节很好,或者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这篇东西还很不成熟,在这种基础上让他们逐渐修改的过程中慢慢完善,同时他们进步也很大。

我们在招博士的时候也一样,也有很深的体会。尤其是瑞华和清玉那一届,他们两个人一篇作品没有发表,但是他们两个人笔试、面试表现都很好,包括张莉老师、清华老师、莫言老师对他们的表现评价也都很好。当时报考的包括我这的那些学生里面,有的已经发表过十多篇,但我一看,我认为写不出来。
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太多了,但是为什么我最后录取她们呢?清玉是有想象力的,瑞华感觉好,是因为这两点,后来他们读博以后作品一篇篇出来。因为不着急,他们都是年轻人,将来走上社会以后还要继续写,我们培养学生不是你现在已经发表了重要作品,而是你将来能否在文学上真正取得成绩的作家,我们不以发表作品来衡量一个作者。这是我们几年工作下来的一个体会。
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一点,我原来对90后作家不怎么关心的,但是自从我们自己的学生以后,我也开始读校外90后作家的作品,说句实在话,我上次跟清华说的,我们真不要做井底之蛙,社会上有很好的90后作家,这个数量相当多,我们还是任重道远的。
苏童:学习写作更大的意思是学习虚构
我到北师大,我原来一直以为自己是来当花瓶的,结果北师大不要花瓶,它真的要园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跟孩子相处确实有当园丁的味道,无论他是学文学创作的学生,他跟现在导师的关系已经不是我们当年想象的师生关系,现在因为也不是私塾学堂的学校,基本我们不能塑造他,如果我们只能呵护他的话有点矫情,但通常来说我们是在做调整和建议。

我从2015年开始到2016年的一届学生,今天在座的有李晓博(陈各)和陈帅、郝文玲,是我的靠前届的学生。我是很欣慰的,陈各虽然写的比较少,但《狗窝》被很多选本收过,我们靠前届这三个学生从某种意义上给我开了一个好头,让我对我的园丁事业有一种比较好的期望。有几张好牌在手上,有的同学写作比较弱的,你也觉得有王炸在手上,也不怕,你碰到优秀的学生他会给你吃定心丸,所以你的园丁事业没有白费,今年这棵花枯了,那边一棵又开了。当然我们做的很多工作就是在具体的作品当中,我觉得就是调整、建议,剪剪枝,施施肥,确实是做这样的工作。
我跟学生的相处真的很民主,一旦你需要,我随时在场,我对学生基本没要求,但是首先你永远不要让老师看到“18岁青涩迷茫的我”,“在校园里如何如何的我”。
我说不要出现这样的句子,有一个原因,因为当一个中学生写作的时候很容易用自己做素材,我说学习写作更大的意思是学习虚构,一定要尽量的把自己先跳开来,或者说你把自己虚涨五岁,你想象一下人生是什么样,虚构就开始了。这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度”,我说不要写你们的青春校园生活,反而到40岁可以写你的中学,现在不要写,现在学习写别人的故事。
我一讲能讲四个小时,不能多讲了,我自己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思,从一开始是某种任务性的,渐渐的跟学生相处,我也蛮有成就感的。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孙庆云
校对 王菲
余秀华儿子上华科大了吗
一年一度的华科大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春讲”“秋讲”,都成为文学的盛会。2019年“春讲”邀请到的驻校讲学着名作家是清华大学教授、茅奖得主格非。4月20日,“春讲”主场活动“喻家山论坛”在华科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举行,围绕“文学与疾病”话题,来自国内外的作家、评论家、心理学家、医学家展开对话。

很多疾病缠身的作家都成了很棒的作家
“文学与疾病”看似是跨界的两个东西,实际上却如影随形。华科大中文系教授刘久明在主持“喻家山论坛”时,做了一个详尽的统计——
从作家层面来说,文学史上,许多着名的作家都是学医出身,他们有的后来弃医从文,如中国的鲁迅、郭沫若,当代作家余华、池莉、毕淑敏,英国的毛姆,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法国的布勒东、俄国的契诃夫等。历史上还有许多作家,终身被疾病缠绕,而文学创作则成为了他们反抗疾病的一种方式,最后他们成了非常棒的作家。如卡夫卡、勃朗特姐妹、契科夫、鲁迅、郁达夫等都是肺结核患者,普鲁斯特多年一直身患哮喘,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幼患有癫痫病,伍尔夫和川端康成一生饱受抑郁症的折磨,农民诗人余秀华自幼就是脑瘫患者。
“有人做过统计,在世界最着名的作家和艺术家中,身心完全健康的人大约只占10%,绝大部分作家艺术家都不同程度地患有各种疾病。”刘久明抛出这样的疑问,“这一现象不由得使我们思考:是什么原因使文学与疾病成为了一对孪生姐妹?究竟是因为疾病激发了作家的悲悯情怀和创作灵感,还是如菲兹杰拉德所言,当一个人痛苦的时候才会变得才华横溢?”这一疑问引发与会专家们从各自不同角度的解读。
“写作能对身体或心理病痛起到抚慰作用”
楚天都市报记者就这一疑问,在会议间歇采访了华科大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春秋讲学”发起人、着名作家方方。
方方说,“一个人患病之后会激发文学创作的才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说得通的。 “当你身体健康时,你是意识不到自己某个器官存在的。写作也类似,在常态情况下,很多东西人是意识不到。当有疾病的时候,打破了常态,人就会陷入很多思考,比如,病会不会治好,死亡之后不能看到这个世界怎么办……各种情绪汇聚在一起,人会表达出更复杂的东西,而文学恰恰需要复杂的情绪和思考,所谓‘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你会拷问自己,拷问人性。很多作家也把写作当成是对自己身体或心理疾病的抚慰,如果不写作,他们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宣泄自己的痛苦。”
“文学是社会的切片,打开的社会相对会更健康”
在文学作品中,有疾病的人也常常成为重要角色,推动故事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有一本书《病夫治国》,作者笔下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或身体上的或心理上的。”在方方看来,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考量,当今社会有“病”的人也很多,比如永远抱怨的人,喜欢吹牛、炫耀的人,特别小气的人,喜欢告密的人……而文学作品是社会的折射,社会的切片,文学作品中的人也是社会上某些人群的缩影。“人群中有这么多病人,文学作品中也都充斥着病人就不奇怪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甚至可以说疾病成就了文学。”
方方拿《巴黎圣母院》举例说,卡西莫多本就是一个患了重病的人,副主教克洛德是心理上有病的一类人,性格活泼、热情似火的爱斯米兰达是一个正常人。“由此,我也想到了心理学的一种观点,认为打开状态下的人,心理问题相对会少一些;而遮蔽型的人,心理问题相对会多一些。推及社会也是一样,打开状态下的社会,相对也会更健康。”
方方认为,“文学与疾病”的关系,从多层次去解读和思考,可以给人不同的启发,是一个很有张力的话题。
楚天都市报记者徐颖 通讯员王均江 钱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