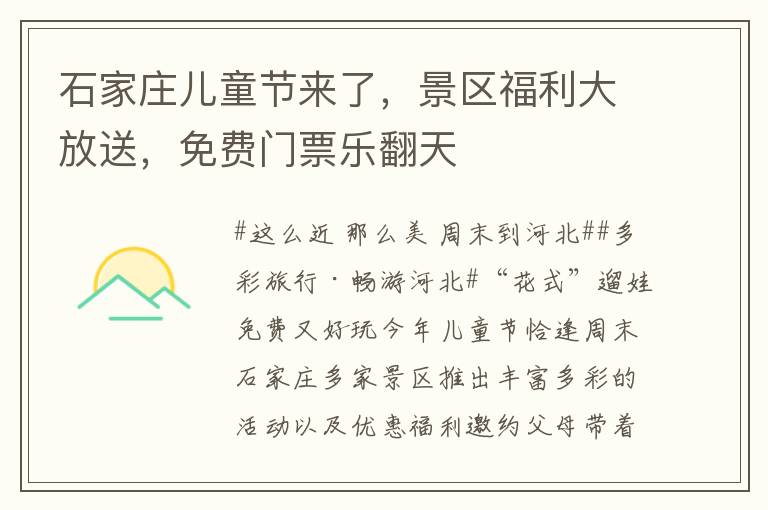(作者: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布克笔记注,本文4500字,内容很丰富,需要您耐心阅读,欢迎留言讨论。
我的观点是要恢复和支撑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大力度的市场化改*。大家有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支撑增长速度的看法,有要加大财政赤字货币政策来恢复经济增长的建议。当然,我不是绝对否定这些,这些可能都需要,但是,我的看法,要将速度恢复了稳定住,重要可能需要大力度的第四次市场化改*。
一、中国未来自然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2.2%左右
1957-1977年,GDP年均增长速度为5%。抽入方面,就业劳动力年平均增长2.6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年平均42%,但有效资本增长率年均为7.5%,劳动与资本替代系数大体为0.3和0.7,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21%。
改*开放以后,就业到2021年为止,GDP年均增长9.24%。投入要素投入方面,就业劳动力平均增长1.4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年均下降到14.1%了,但有效资本年均增长率为9.07%,劳动与资本的替代系数分别为0.5和0.6,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在0.8%左右。
未来增长推算,最基本的算式是索洛模型。以此简单匡算,2023到2037年间,GDP年均增长速度也就2.2%左右。理由是,投入方面劳动力年均增长-1.1%已经是一个基本确定的数据,资本增长根据人口变化和老龄化情况,年均增长可能为4%左右,未来我们提高劳动贡献比,资本边际产出率会下降,平均替代系数如果为0.5和0.5,则要素投入产出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也就1.45左右,假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会增长与改*开放以来的水平一样,为0.7%。
国内学界和大部分人士,对此计算结果都有疑问,为什么预测这么低?我在大学博士学的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供给侧的生产增长模型。我觉得这是一个体制既定,在市场经济情况下的一个增长函数,这个算式仿真和推演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有误。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机构,包括最近日本的一个研究机构对中国未来增长速度看低,与这种算式有关。
二、将速度支撑侧重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风险
索洛模型前面有一块是全要素生产率。如果我们未来要达到年均增长速度4.73%,除了投入产出部分,要使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年均从改*开放以来的0.7%提高到3.28%,如果要增长5.5%,则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增长4.05%,而如果要将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提高到增长部分的80%,则年均增长速度要提高到4.35%。
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认为可能性很小。
1971-2019年间,荷兰罗格宁根大学计算的数据,日韩法德英美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将近半个世纪。日本平均年增长率是0.51,韩国是1.69%,法国0.72%,英国0.58%,德国好一些1.05%,美国是0.59%。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占GDP比例日本21%,韩国24%,法国33%,英国24%,德国较好是52.9%,美国21%。没有看到这些发达国家GDP里全要素生产率部分能贡献增长的80%,较好的就是53%。可以看出近半个世纪中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高是的韩国1.67%,平均对GDP增长贡献比例*高的是德国52.9%。中国1957年到1977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1.21,1978年改*开放到2019年数据是0.696%,占GDP比例7.4%。
我这两年读了两篇论文,也是在研究时发现的。琼斯根据欧美1980-2000年研发人员数量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研究,发现研发人员向上向右的增长的曲线并没有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曲线的向上向右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长期平缓。
菲斯佩奇对此评论到,无论创新投入如何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一个平缓的趋势,而不是J型增长或者S型增长状态。从前面的数据看,日、韩、法、德、英美都在0.5%-1.0%之间,除了韩国高一些,未来15年中国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增长速度能够达到德国1%的水平吗?能达到韩国1.69%的水平吗?能达到超过他们,比如达到2%的水平吗?我觉得希望不大。
如果有我们会指数和S型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想法,影响推动增长的决策,则可能会有较大的风险。
三、财政货币扩张政策稳定经济增长也可能有较大的风险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凯恩斯觉得原因是总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了,原因就是消费者有货币持有偏好,投资者有保持储蓄偏好,导致国民经济循环中流动性不足。因此,在萧条的时期,凯恩斯的想法就是你得搞财政赤字,扩大货币供给,注入流动性。流动性不足导致了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达不到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哈罗德—多玛增长和钱纳里双缺口等模型,特别是前一模型,在工业化初或工业化中期,资本边际收益率比较高的时候比较适用,但是现在也不适用了,加大投资这些增长模型的建立。
我觉得中国的增长潜能在什么地方?我认为看1957年到1977年与1978年到2021年对比以后,要素投入大幅度的下降,但是产出年均增长9.24%。我认为在体制,过去那个体制中生产要素、消费潜力和财富价值等,浪费闲置淹没低利用等规模太大,禁锢在体制扭曲中。这种体制扭曲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的。比如财政政策能解决户籍问题吗?货币问题能解决国有企业资本产出低效率问题吗?它解决不了。因此,我觉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是稳定增长的配角。
1978年到1992年启动的两次高增长,主动力是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对生产、消费和价值能力的释放。 2001年启动的高增长主要是开放外贸体制,与国际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的改*,还有土地有偿出让和城镇住宅资产化改*推动的。其中,2009年我们用了4万亿刺激,这确实是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但到2012年以后增长速度还是跌到了8%以下,还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和下行压力。
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我们今天要防止的是什么呢?如果是特大力度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结果可能会造成滞胀的局面。
四、只有大力度的市场化改*才能实现经济恢复和中高速增长
1.经济增长奇迹的潜能来自于体制改*
温故而知新,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由体制改*释放生产力而获得。1978年到2021年经济增长一半多来源于改*。一是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改*开放前的年均增长-1.21转成了改*开放以来的年均0.7%。改*开放后的44年中,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实验室计算,年均总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3.32%,但我们分解,其实除了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外,其余的体制改*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
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年均大体为1.99%,城镇住宅原来是生产资料,改成有价值的财富资产了,这种房子二手交易零到市场价溢值带来的增长大概0.53%。还有大规模土地交易到市场价溢值各种方式进入生产法的增加值核算年均增长率为2.57%。改*创造的GDP增长率占了5.09%,剩下就是二元体制自然增长速度为4.15%。
2.生产侧的增长潜能和改*
我们研发了一套二元体制经济增长内生数理逻辑和计算方法, 我们以此仿真和推演供给侧改*增长。体制剩余性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盘活释放增长潜能,要素利用效率提高,年均会带来1.4%左右的增长。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资产化改*,你让他交易,它的溢值潜能年均大概也在1.4%左右。另外,我们还提了个建议,调水增加土地,扩大可利用土地增长这块再加上它的土地资产化改*,年均增长潜能大概0.45%左右。未来总的经济增长实现一个年均5.5%的增长。从数理逻辑和算法上都没问题,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因为生产、需求和财富领域中,存在大量的浪费闲置淹没低利用。
3.需求侧的改*增长潜能
我们也做了均衡增长逻辑和算法设计。生产侧的经济增长受到需求侧市场购买可能性边界的约束。目前供需失衡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但是重点是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刚才晓河院长也说了,市场经济国家标准值和我们的差值,一般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在60%-65%,消费占GDP比例要到50%以上。我们1983年时,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为62¥,消费占GDP比例50%。去年的这两数据是多少呢?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不到44%,消费占30%%。要是在均衡增长的可视化系统上,你把占比指针往再少里拨,经济增长速度就下降,你把占比往多调,经济增长速度就上升。因为它是关联的。
那么,居民收入和消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体制扭曲性问题呢?
现在从二元结构上阻碍人口从低收入区域和行业向高收入区域和行业流动,这几年劳动力倒流。土地交易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房价收入比,原来按城镇收入算,后来很多学者提意见,城市化好多是农村的孩子毕业以后到城市买,还有农民买,你们按城镇居民收入算房价收入比不对的,后来我们调成全国人均收入房价比,一下子提高到10.9了,标准值大概是6,有些国家是3,这是转移了居民收入和挤出了居民消费。
政府对居民提供教育、医疗、养老和廉租等服务保障不足,逆向替代,居民就得自己支付,又占用了居民的收入和挤出了居民的消费。因此,未来的改*,人口迁移市民化、土地收益分配、住房供给、政府居民服务保障四等体制必须得配合改*,得提高居民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需求。
一是假定广义技术进步的自然增长速度,以及产出的增长速度是2.25%。
二是人口和迁移劳动力流动体制改*,即让低收入的农村农业和区域向高收入的城镇工商业和区域流动,会形成年均1.1%的消费支出增长。就是把户籍彻底放开,子女教育不再城乡歧视,取消房屋异地限购之类的,全放开,如没有当地户口不能买车什么的。
三是放开城乡和农村土地交易资产化,直接入市,农民分配和政府收税,这会带来年均1%的消费支出增长。
四是居住体制房价要向合理房价回落,年均有0.6的消费支出增长,主要是房屋的供给要多元化。房屋的土地供应要竞争化,直接进入建设市场。
政府提供廉租房,各个国家在城市化阶段都提供过这这方面政府对居民居住民生的帮助,包括美国都提供过。政府更多的提供医疗养老、廉租这些消除居民逆替代支出。这个大概能带来0.55%的年均消费支出增长。
最后一图是我们1978年以来改*与经济增长历史的展现,以及未来改*与经济增长仿真和推演。1976年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后来反弹,1978年开始改*,后来风波,又开始批,最后南巡讲话,最后又跌到金融危机以后,1999年,季度跌到6%,最后是城镇住宅有偿和资产化改*,1998年开始,加入 WTO,土地有偿出让大规模招投标改*铺开,一直推到这儿,最后2008年下跌以后又有四万亿的刺激。所以,我的想法是可能还是要大力度改*才能使经济增长恢复起来,并保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可以努力,但不要幻想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辅助,但不要在财政货币政策上绕圈子。1980年是预算1亿项目投资,40%是工资支出,现在高速公路都降到10%了,投资大部分流不到居民收入和消费那儿。所以,我就想中国的增长潜能大部分锁定在体制扭曲中,只要改*就释放,不改*就不释放,盘活释放就是经济的新增长潜能。这也是我们的历史和经验,它不是凭空出来的结论。
大家也可以看出,改*的边际效应递减,没有再一次大力度的改*增长速度是不会起来的,我们还是要从如前三次大力度市场化改*入手,靠前次大力度的改*和第二次改*,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了20年。第二次我们加入WTO和出让土地和城镇住宅资产化改*,又使20余年中经济平均增长了9.24%。我们能不能开启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再持续10到15年,我们把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拉到5.5%,这样我们的经济完全可以翻一番,我们完全可以初步建成现代化的国家。
总结一下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由提高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和扩张财政和货币政策稳定住。
计划向市场发育释放和开放及资产化改*促进中高速增长的边际功效已经越来越弱,房子盖的差不多了,地也卖不动了。
从阶段上看,到了计划与市场二元并存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轨的阶段了,建议启动第四次大力度的体制改*。而且现在是个机遇期。2023年应当壮士断腕,以非凡的魄力,启动如前三次大力度的改*,才能把增长速度稳定和支撑在年均5.5%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