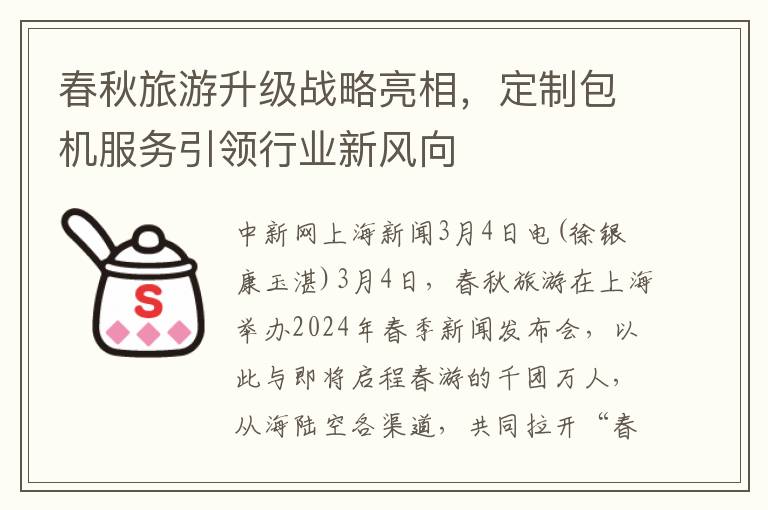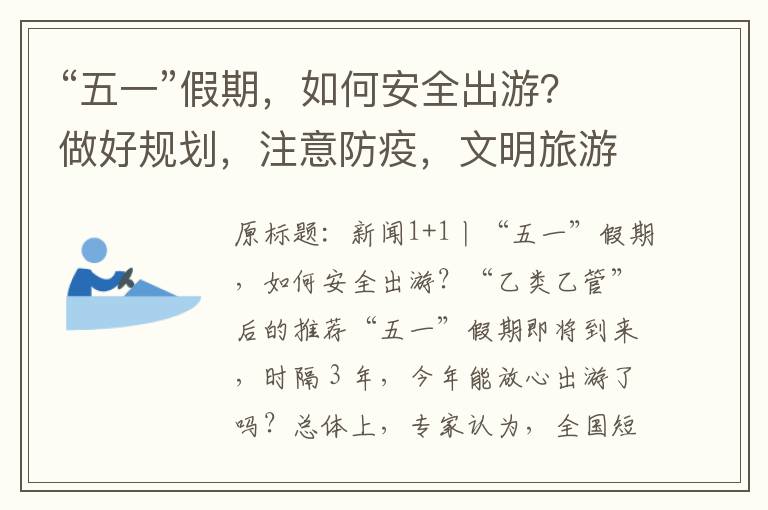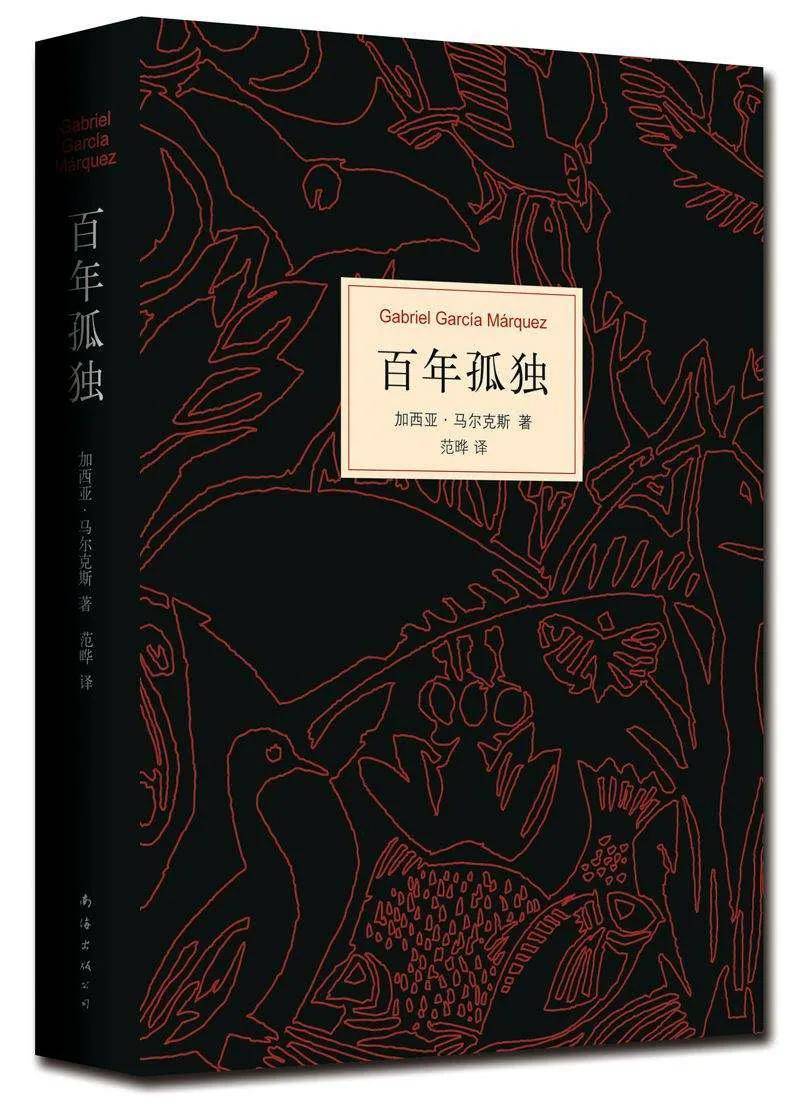
在奥雷里亚诺一世谋划起义的时候,阿尔卡蒂奥二世(他哥哥的私生子)已长成一个身材魁伟的少年,因战争的迫近越来越兴奋。在学校里,比阿尔卡蒂奥二世还要年长的学生跟刚学会说话的孩子混在一起,自由派的激情在那里传播开来。他们谈论着枪毙尼卡诺尔神甫,将教堂改成学校,实现自由恋爱。
那时奥雷里亚诺一世还没最终决定发起战争,并试图抑制他的狂热,劝他要小心谨慎。阿尔卡蒂奥二世听不进他冷静的说理和对现实的客观估计,当众斥责他性格软弱。
目睹保守派惨无人道的暴行后,奥雷里亚诺一世终于下定决心,并带领一群志同道合者发动了一次近乎疯狂的行动,二十一个不到三十岁、用餐刀和尖铁棍武装起来的男子由他率领,奇袭军营,缴获武器,并在院中将上尉和四个杀害那女人的凶手枪毙。 当夜,在行刑枪声响起的同时,阿尔卡蒂奥二世被任命为镇上的军政首领。
这次行动后,奥雷里亚诺一世自封将军,带着一起起义的二十一个人投奔维多利奥·梅迪纳将军。
“我们就把马孔多交给你了。”这便是他临行前对阿尔卡蒂奥的全部嘱托,“我们好好地交给你,你争取让它变得更好吧。”
阿尔卡蒂奥二世对这一托付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从梅尔基亚德斯一本书的插图获得灵感,发明了一套带饰带和元帅肩章的制服穿上,腰间还挎着那位被处决的上尉的金穗马刀。他将两门火炮设在镇子入口,让他昔日的学生统一着装,他们听了他的演讲群情激奋,全副武装四处巡逻,给外人以坚不可摧的印象。
从掌权的第一天起,阿尔卡蒂奥二世便显露出发号施令的嗜好。他有时一天颁布四份公告,想到什么立即宣布实施。他推行针对十八岁以上男子的义务兵役制,将下午六点以后还在街上行走的牲畜都征作公用,还强迫成年男子佩戴红袖章。他将尼卡诺尔神甫幽禁在神甫寓所,并以枪决相威胁,禁止他主持弥撒或敲钟,除非是庆祝自由派的胜利。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不容置疑,他下令让一支行刑队在广场上练习射击稻草人。起初没人当真。归根结底,那不过是些还上学的孩子在扮大人。然而一天晚上,阿尔卡蒂奥二世走进卡塔利诺的店里,乐队的小号手吹出夸张的调子跟他打招呼,引得客人笑声连连,他当即以藐视当局的罪名下令将小号手枪决。凡是抗议的人,一律关进他在学校设立的一间牢房,戴上脚镣,只给面包和水。(是不是有点像文革时期的红卫兵)
“你是个杀人犯!”乌尔苏拉每次听到他任意妄为的消息都会向他大吼,“等奥雷里亚诺知道了,会把你给毙了,我第一个去放鞭炮。”但这些都无济于事。阿尔卡蒂奥继续强化他那毫无必要的铁腕手段,成为马孔多有史以来最残酷的统治者。
“现在尝到不同滋味了吧,”一次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他叔叔奥雷里亚诺将军的岳父)这么评论道,“这就是自由派的天堂。”话传到了阿尔卡蒂奥二世那里。他领着巡逻队闯进屋门,砸烂家具,殴打女眷,把摩斯科特拖走了。乌尔苏拉一边满心羞耻地哀号,一边挥舞着涂过柏油的马鞭,穿过镇子冲进军营的院中,这时阿尔卡蒂奥二世已准备就绪,正要下令执行枪决。
“我看你敢,杂种!”乌尔苏拉喊道。
阿尔卡蒂奥二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第一记鞭子就抽了过去。“我看你敢,杀人犯!”她喊道,“婊子养的,你把我也杀了算了,省得我丢人,养了你这么一个怪物。”她毫不留情地鞭打,一直把他逼到院子深处,像蜗牛似的缩成一团。摩斯科特被绑在柱子上,昏迷不醒,原先立在同一位置的稻草人经受演习的弹雨早已支离破碎。行刑队的小伙子们四散奔逃,害怕乌尔苏拉拿他们出气,但她看都没看他们一眼。她任凭身上制服破烂的阿尔卡蒂奥二世在一旁又疼又怒地吼叫,解开绳索把摩斯科特带回了家。离开军营前,她还释放了那些囚犯。
从来没有人告诉阿尔卡蒂奥二世他的身世,庇拉尔·特尔内拉,他的母亲,曾经在照相暗室里令他热血沸腾,对他而言,她是无法抗拒的诱惑,甚至差点让他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好在他的母亲很是机智,付了一个名叫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女孩子,她是处女之身,五十比索,毕生积蓄的一半,让她代替自己上了阿尔卡蒂奥二世的床(一个母亲对儿子还的爱)。阿尔卡蒂奥二世多次看见她在父母开的日用品小店里,但从未留意过,因为她拥有一种罕见的美德,只在适当的时机现身,平时都无人察觉。但从那天起,她便缠上了他,就像到他腋下寻找温暖的猫。她每到午休时间就来学校—她父母收了庇拉尔·特尔内拉的另一半积蓄,也不加阻拦。晚些时候,政府军将他们赶出了学校,两人便在店后的黄油罐头与玉米袋中间恩爱。到阿尔卡蒂奥二世被任命为军政首领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美人儿蕾梅黛丝二世)。
再后来,奥雷里亚诺将军行动受挫,委派一个使者来向阿尔卡蒂奥报信,告诉他应当放弃抵抗投降,以换取敌人保证自由派生命财产安全的允诺。但阿尔卡蒂奥没有动摇,他下令将信使关押起来直到弄清他的身份,并决心誓死守卫辖地。
三月末,几星期以来紧张的平静被尖厉的军号声猝然打破。随后一声炮响,教堂的尖塔轰然倒塌。阿尔卡蒂奥二世的抵抗决心与疯狂无异。他手下不过五十来人,装备低劣,每人至多能分到二十发子弹。但这些人,他旧日的学生,受他那慷慨激昂的宣言所鼓动变得热血沸腾,时刻准备着为一项无望的事业献出生命。
纷乱的军靴声,互相矛盾的号令声,令大地震颤的炮火声,阿尔卡蒂奥二世领着参谋部冲向抵抗前线。他没能到达通往大泽区的路。街垒都已被清除,守军在无遮无挡的街道上作战,他们先用步枪直到子弹耗尽,然后用手枪对步枪,最后展开肉搏战。
在镇子失守前,一些用棍棒和菜刀武装起来的妇女冲到街上。阿尔卡蒂奥二世在混乱中发现阿玛兰妲正像个疯子一样四处找他,身上还穿着睡衣,手持老布恩迪亚的两把老式手枪。他把步枪交给一位在战斗中弄丢了武器的军官,拉上阿玛兰妲逃向邻近的街巷带她回家。乌尔苏拉等在门口,纷飞的流弹已在邻居家墙上打出一个窟窿,她却全不在乎。雨停了,街面变得像泡化的肥皂又软又滑,而且黑暗中辨不出远近距离。阿尔卡蒂奥二世把阿玛兰妲交给乌尔苏拉,想去对付两个从街角胡乱开枪的士兵,但老手枪在衣柜里收藏多年之后失去了效用。乌尔苏拉用身体护住阿尔卡蒂奥,想把他拉进家门。
“快进来,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喊着,“别再发疯了!”
士兵们瞄准了他们。 “放开那个男人,女士,”其中一个士兵喊道,“不然后果自负!”
阿尔卡蒂奥二世把乌尔苏拉推向家门,随即投降了。很快枪声停息,钟声敲响。不到半个小时,抵抗被彻底粉碎。阿尔卡蒂奥的人一个也没活下来,但在战死前拉上了三百个士兵陪葬。
天亮的时候,经过军事法庭的即时审判,阿尔卡蒂奥二世被判处枪决,在公墓的墙前执行。在生命的最后两个小时里,他想着八个月大的女儿还没有名字,想着即将在八月出生的孩子。他想着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昨天晚上他还给她留了一头鹿腌起来准备星期六中午吃;他想念她披散在肩头的发丝和她仿佛出自人工的睫毛。他想着他的亲人,并无感伤,只是在严格盘点过往时发现,实际上自己是多么热爱那些曾经恨得最深的人。
置身于满目疮痍的学校,他曾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到权力带来的安全感,他曾在一旁几米开外的房间里初尝情爱的滋味,阿尔卡蒂奥二世感到这样煞有介事的死亡不免可笑。其实他在意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因此听到死刑判决时他心中没有恐惧只有留恋。直到被问及最后的愿望,他才开口。 “告诉我女人,”他声音非常平静,“给女儿起名乌尔苏拉。”他顿了一下,重复道,“乌尔苏拉,跟她祖母一样。再告诉她如果生了男孩,就叫他何塞·阿尔卡蒂奥,但不是随他伯父的名字,而是随他祖父。”
走向墓地的路上,细雨绵绵不绝,阿尔卡蒂奥二世望见星期三的曙光闪现在地平线上。留恋之情随着晨雾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好奇感。当行刑队命令他靠墙站好的时候,在被一排黑洞洞的枪口瞄准的瞬间,他听见梅尔基亚德斯仿佛教皇通谕的吟唱,听见还是处女的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在教室里迷离的足音,同时鼻中感受到曾在蕾梅黛丝(他的婶子,奥雷里亚诺将军的妻子)尸体鼻腔内发觉的冰块般的坚冷。“啊,糟糕!”他想起来了,“我忘了说,如果生女儿,就叫她蕾梅黛丝。”一时间,随着撕心裂肺的剧痛,折磨他一生的全部恐惧重又涌上心头。上尉下令开枪。阿尔卡蒂奥二世几乎来不及挺胸抬头,就感到不知从哪里流出的滚烫液体在大腿间烧灼。
“浑蛋!”他喊道,“自由党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