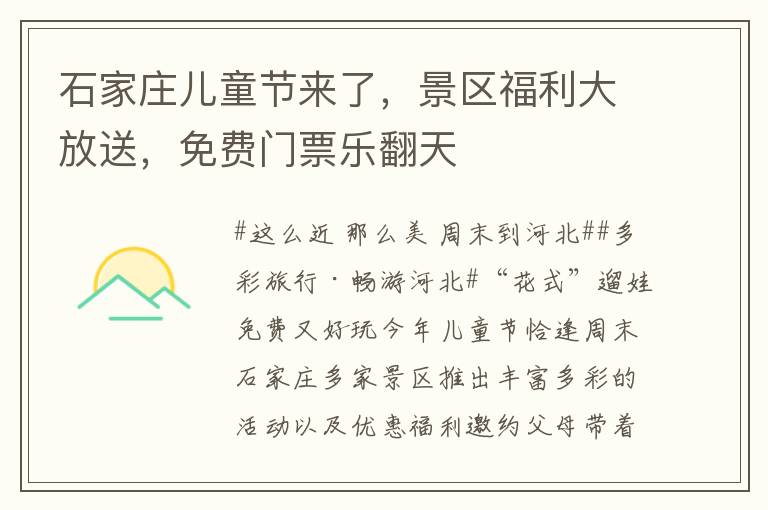田霏宇来自美国费城,原名,最近十余年在中国从事当代艺术的译介、策展工作,2011年起担任UCCA馆长。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图)
2021年12月11日,首届迪里耶当代艺术双年展(The Diriyah Contemporary Art Biennale)将在沙特阿拉伯迪里耶JAX创意区举办。该双年展是沙特首个国际双年展,随着西亚地区在国际地缘关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西亚地区的文化也迎来空前的发展。双年展的策展人是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兼CEO田霏宇(Philip Tinari),主题是“摸着石头过河”(Feeling the Stones)。
在过去十余年时间里,这位策展人,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全球化的问题上,提交了一份内容丰富的答卷。而在田霏宇担任UCCA馆长期间,他主导策展了刁德谦、谢德庆、罗伯特·劳森伯格、威廉·肯特里奇等世界艺术名家,以及顾德新、王兴伟、赵半狄、徐冰、黄锐等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个展。近来,田霏宇又联合国外的美术馆和基金会策展了毕加索、安迪·沃霍尔等世界艺术大师个展,未来还将有亨利·马蒂斯。
过去二十年,全球艺术市场发生了显着增长,其中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更是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根据Artprice的一份统计报告,从2000年到2019年,全球艺术市场交易额从0.92亿美元增长至19.93亿美元。其中,中国艺术市场交易总额从大约100万美元跃升到6.59亿美元,2019年位列世界第二,2020年则超越美国暂列第一。
中国艺术市场开始加速发展之时,美国费城青年田霏宇开始将目光投向这片热土。20世纪末,正在杜克大学就读的田霏宇,因缘际会结识了来到杜克大学访问的徐冰,旋即参与到了徐冰的“烟草计划”,他感受到中国当代艺术原来这么有趣,这么深刻。随着徐冰的“烟草计划”在世界多个城市的循序展开,一个由烟草、杜克、中国组成的关系网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位费城青年追踪着徐冰的“烟草计划”,开始畅想他的艺术生涯。
正是在杜克大学,田霏宇学习了当时并不时髦的汉语。毕业后,田霏宇获得奖学金,第二次来到中国深造,赴清华大学进修一年。此后,田霏宇在多个领域展开探索,但他没有在中国停留很久,又到哈佛大学开始新的读书生涯。在《华尔街日报》实习期间,田霏宇感知到美国媒体行业的衰落与改变,他转向艺术行业。经过苏富比半年的工作,田霏宇再次发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广阔前景,而后他又来到中国。田霏宇先后在Artforum中文网做创始主编、《艺术界 LEAP》做编辑总监。
2011年底,在UCCA收藏拍卖风波过后,刚报道完该事件的田霏宇,正式加入了UCCA,成为UCCA第三位馆长。2016和2017年,UCCA随着机构重组,成功转型为UCCA集团,田霏宇担任UCCA集团CEO。田霏宇与观众的对话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看展已经成为文化消费或者娱乐消费很重要的一部分,展览似乎和电影、戏剧放在了同样重要的位置。”田霏宇说。

中国当代艺术和世界艺术都是UCCA展览的重要系列,图为2021年11月19日的该馆现场,观众正在观赏意大利国宝级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在中国的首次个展。 (视觉中国/图)
“打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南方周末:在2000年前后,你就读于杜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后来又回到了中国。为什么你当初来到中国选择做媒体?你曾经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有一个比较明朗的预期,后来的发展和你当初的预期有何不同?你对当代艺术史的看法和认知是否带有一种微妙的外部视角?
田霏宇: 我很熟悉西方媒体和艺术圈对中国当代艺术根深蒂固的误解。早期我做的很多工作,其实都有一个共同期待,就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打破、去丰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常规判断。最初,我没有选择去《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做记者。面对西方世界忽视现实,做道德判断的立场和内容,我感到很不舒服。
刚好,我在中国发现,艺术领域、艺术世界还很开放,而且还没有成型。当时,我年轻,文笔好,翻译顺达,摸索着就进来了。通过早期的实践,我也更了解艺术领域的丰富性。早先几年,我也负责为某些美术馆来访的董事团做报告和相关安排,后来又在《艺术论坛》(Artforum)、《艺术界 LEAP》工作。那时我希望自己兼具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也很期待两种视角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我不认为做《艺术界 LEAP》这本刊物仅仅是将中国介绍到国外,我所实践的,所抵达的,是基于对文化生态的关怀以及对其复杂度的理解,创造出一个自洽且权威的媒体,它能够用潇洒的立场来看待中国当代艺术。当时,我觉得有这样一种话语的定位和立场,也是很有意义的。但十几年后的今天,我的兴趣发生了变化,我现在更看重艺术对看似与之无关者的影响。
南方周末: 你在连接的是两个开放性,一个是早期全球化所面对的开放性,或者说不完全的开放性;另一个是现在展现出的新的开放性,包括艺术本身,当代艺术现场本身,以及你所提及的观众。你觉得当代艺术的开放性会如何变化?
田霏宇: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近些年,很多当代艺术实践者都碰到了开放性的边界。2017年,白人艺术家达娜·舒茨(Dana Schutz)画了一幅1950年代黑人伙伴爱默特·提尔(Emmett Till)的画像,借此表达了African American(美国非裔)的悲剧。这件作品出现在当年的惠特尼双年展上,展出开始后,它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美术馆也很难判断这个作品是否应该撤下,“该留还是该走”。
还有就是1950年代比较重要的画家菲利普·加斯顿 ( ),他的画作涉及了屠杀、暴力等议题。有人认为这样的图像会引起大家的情感创伤(),也有人直接发表了相当强烈的抗议。但是加斯顿本人显然不是在歌颂三K党,他要表达的是人们内心的黑暗,以及暴力和野蛮的根源。其实,他作品的艺术思想层次很丰富,但是在当下的语境不允许我们讨论。
总的来说,开放性的边界很难掌握。但是,艺术最后还是会给想要挖掘的人带来意想不到的体验。
南方周末: 根据Artprice的一份统计报告,从2000年到2010年再到2019年,全球艺术市场交易额从0.92亿美元增长至11.45亿美元又增长至19.93亿美元,最高拍卖纪录从220万美元增长至1690万美元又增长至9110万美元,销售量从1794件增长至2960件又增长至5874件。全球艺术市场如此蓬勃的增长,意味着什么?
田霏宇:艺术实际可以分成几个层级,可能在顶端层级,艺术更多体现为资本分配和交易。艺术品能够在金融市场占据今天这样的位置,充分表明了艺术品具有可靠性和可携带性。在大资本操盘的情况下,艺术品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回报比。不久前,哈里·麦克洛维(Harry B. )离婚,他的收藏也流入市场,苏富比为此开了一个专场,麦克洛维收藏艺术的历史已经有五十年了,他的收藏包括特别好的安迪·沃霍尔,特别好的阿尔伯托·贾柯梅蒂和特别好的马克·罗斯科。
另外,艺术市场的发展趋势,也和当下的资本两极化、贫富分化等问题密切相关,艺术市场既是一个后果,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大部分人都不在金融层面工作。但是,新贵们也会收藏一定数量的艺术品,比如在北京当代博览会上,很多价位在几万到几十万之间的作品,其买主可能就是这些新贵。他们不只出于投资的考虑,还有美学诉求上的考虑。无论如何,画廊和大部分艺术家都在这个艺术市场体系内运作。
田霏宇近年来越来越重视观众。图为UCCA2021年展览中的表演艺术交流。 (受访者供图/图)
中国当代艺术的全球化
南方周末: 从2000年到2019年,美国的艺术市场增长率为1023%,这个增长率在欧美世界并不算高,而中国的增长率则高达64170%。2000年,中国艺术市场的交易额大约100万美元,2019则跃升到6.59亿美元,位列第二,2020年则超越美国暂列第一。目前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空间在哪?增长还会持续吗?
田霏宇: “增长会不会持续”,1996年,所有北京画廊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原始,也很有趣。我觉得,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前不久,苏富比的两位女高管艾米·卡佩拉佐(Amy )与寺濑由纪(Yuki )联手成立了Art ,主打亚洲艺术场和拍卖。现在,西方当代艺术市场的边际空间比较小,与之相比,亚洲的市场就有很大的发展前景,还有很多可以发掘和探索的疆域。几周前,一位叫丁一潇的年轻人在山东日照建立了潇美术馆。他从2019年开始收藏,现在已经有了一千多件藏品。纯粹从数字看,中国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做艺术市场。未来,这个趋势所能承载的文化意义,还是待定的,但中国艺术市场已经走向全球化。
南方周末: 根据Artprice的数据,前1000名当代艺术家,中国有395名,超过其他进入前十的国家的总和。在最近十年,中国各个数据都开始独步全球艺术市场。但与此同时,为什么中国的艺术家的实际影响力却比不上数据?中国离成为全球艺术市场的引领者,还有多少路要走?
田霏宇: 这个问题很难准确回答。数据的确体现了一种偏向,但可能很多东西只在内部循环,而不是流通进全世界。近些年,也有人会重新考虑提升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艺术史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个意见还是有建设性的。
南方周末: 中国艺术家会凭借这么强的数据,很快进入全球艺术体系里吗?
田霏宇: 现在还有一些隔阂,但一些个案或许很有趣。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们一方面会在国内的场域谋求好的发展,一方面也在有选择地和国外画廊合作,或者到国外做展览,以获得中外同等的地位和身份认同。但是,操作起来非常困难。
南方周末: 全球主要的双年展在创造艺术明星和艺术大师上可以说功不可没,尤其是对于过去某个阶段的中国来说。1993年,廖雯第一次来到威尼斯双年展,她满是好奇和期待。但后来,中国艺术家和策展人越来越不热衷于“走场”。两位策展人在不同时间作出的回应,既代表了不同的立场,又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参与的心态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田霏宇: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在1990年代特别明显。1980年代,艺术家几乎只存在于其他艺术家的视野,存在于刊物、会议等形式上,相对封闭,但内部场域的交流还是很丰富。1990年代,很多偏实验性的出口消失了,艺术家下海的情况也比较多。种种因素的作用下,艺术市场体系和评价体系都没有那么好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们都过分期待和依赖海外的机会,比如商业机会、曝光机会等等。你所说的现象也就出现了。这些现象未必是对全球化的反思和批判,很多艺术家很可能还是在借批判全球化,来思考自身的叙事,思考在外部境遇下的内在处境。
2000年后就好很多,国内形成了自由的市场体系,相对良好的媒体系统,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基本上可以满足绝大部分年轻艺术家的野心。
南方周末:费大为曾调侃,中国艺术并没有给威尼斯双年展带来什么。这自然也并非实际情况。但中国艺术家会更看重自己的文化身份,尤其是欧美世界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身份。侯瀚如早就指出了这个问题。一个中国艺术家进入全球艺术现场仍会强调自身的中国身份吗?
田霏宇: 我觉得可能是个人选择。在短暂的十年时间里,中国艺术家从边缘的身份,转变为新权力和新权威的身份,归根结底可能还是中国艺术内部的力量以及其周全的体系。有这么好的体系和力量,何必非要到国外。
中国民营美术馆骤增之后
南方周末: 最近十几年,中国迎来了建设美术馆的潮流。得益于资金、政策、设计的便利,大量的民营博物馆和美术馆出现在一二线城市。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田霏宇: 民营美术馆的出现,意味着是社会和政府支持当代艺术的持续发展。最近二十年的文化政策,都很欢迎各式各样的艺术机构,也给艺术机构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比如,我在上海调研时发现,UCCA Edge所在的上海静安区就希望引进更多民营美术馆,以此来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
这些民营美术馆出现的原因有很多种。有的是藏家积累一定的藏品,希望做一个展现;有的是企业想承担社会责任,希望做出超出传统企业范围的实践,设立基金会,建美术馆。或者像UCCA,UCCA希望吸纳不同的观众群体,希望美术馆可以凝结成一个品牌。
南方周末: 你在UCCA的十余年里,越来越强调观众。策展和观众、学术和流量是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
田霏宇: 学术的问题,流量的问题都没有这么简单的对立和冲突,在我的思考里,学术和流量分属于不同的方面和方案。美术馆需要与时俱进,不仅中国,整个世界都是如此,全世界的美术馆都越来越欢迎观众,越来越和现代科技、社交媒体捆绑在一起。但这并不损害那些优秀美术馆具体的定位和影响力。UCCA希望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方法。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是让学术和流量达到一个平衡,让学术和流量相互助益。
南方周末: 你如何看待研究型的展览?国内有一批优秀的独立策展人,至今在做研究型、偏实验的展览。
田霏宇: 研究型的策展方式在今天仍然有用。不论是美术馆,还是整个艺术市场,做探索、做实验,还是应有之义。研究性策展,带有总结性、批判性、艺术史面向的探索,这种方式在国内可能还较少。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希望能做这样的工作,把这些展览的筹备期拉长,做更多的研究。现在,一个展览接一个展览,总有点匆忙。
南方周末: 现在是不是有学术跟着市场走的现象?
田霏宇: 也会有。市场跟着学术走才是较为准确的方向。学术导向、市场导向,其实也很难区分开。具体做选择时,艺术机构一般都会很谨慎。有的时候,市场导向是很准确的,这个艺术家可能很受市场认可,也有一定程度的学术价值。如果单纯看市场,一个市场表现很好的艺术家,他的展你做还是不做?你做,会被认为跟风;不做,会被认为你想批判。这种情况就需要艰难的选择。
南方周末:UCCA展览策划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世界艺术和世界艺术大师,从2019年的“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开始,这个维度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你开始注重那些超经典艺术大师。毕加索是一个例子,安迪·沃霍尔、马蒂斯也是如此。这个方向是毕加索的轰动效应的结果吗?
田霏宇:那个时期,美术馆一直在寻找新的可能性。做大型展览会吸引一些新观众,有可能形成新的关系,吸引观众成为未来的观众。毕加索大展给UCCA带来了非常意想不到的突破。整个展览的观众量有35万,门票收入超千万,美术馆参展人数和票房创新高。
更重要的就是,通过大师展,我们找到了和观众的契合点。很多观众一开始只是听说过毕加索,他的形象和作品出现在教科书、广告、口头传播中,但很多观众其实根本没有了解过毕加索,以及他的作品。大师展的效用就体现在这里,大师很多时候一直都只是一个符号,他是以符号的方式,而不是以艺术、思想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认知和想象里。UCCA做大师展就是要打破这堵墙,将大师形象化为艺术品、思想方法,以及人生故事。要知道,符号的价值不大,只有当符号成为艺术品,成为具体的思想方法,这个符号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应。
现在因为疫情我们没有出国的机会,想看这类艺术品,并不能时不时去巴黎、纽约、伦敦。但在国内,大部分情况下,观众还是可以来北京、上海看看毕加索、安迪·沃霍尔。这就是大师展,区别于网红展的地方,他们还是跨越时间、地域,以及文明具体的隔阂的。
南方周末: 就你的经验而言,观众对研究型展览的接受度如何?
田霏宇:可能还是少数人感兴趣,但我们也会刻意引导。比如我们会把“王拓:空手走入历史”和“成为安迪·沃霍尔”的入口做成同一个。
“不见得拍照打卡有多么低级”
南方周末:UCCA经历过两次提价,一次是2016年“劳森伯格在中国”提到60元,一次是“徐冰:思想与方法”提到100元,后续的大展很少低于100元。为什么门票价格大幅度增加了?和世界其他大都市相比,这个价位合理吗?
田霏宇:上海的美术馆的展览门票价格都比我们高很多,而且从具体情况看,中国的美术馆票价变化一般是从上海开始的,它是文化系统运作的结果。从整个世界来说,美术馆收门票是理所当然的事,门票收入是美术馆运作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从中国美术馆的发展状况来看,门票价格的增加主要是市场运作的结果。以UCCA为例,随着门票收入的增加,我们可以更充分地开展我们所期待的活动。
南方周末: 随着观众的人数增多,人们看展的方式也变得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打卡也流行了起来。UCCA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兼顾不同的观看方式?
田霏宇: 最近几年,看展才成为主流,但我们对观看行为、展览空间的经营则由来已久。现在看来,我们所做的尝试得到了很好的接纳和回应。每个大型展览,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设计团队参与我们的策展布展工作。我总希望观众可以舒适、享受地看展,很多有趣、有新意的思考,可能就在这个惬意的观看中产生了。
具体来说,每一个展览,大展厅、小展厅都会有新的展陈设计,大展厅也会有非常显着的空间改造。比如“曹斐:时代舞台”,大展厅里出现了一个挑空的二层展览空间,很迷幻,但很真实,这个设计出自Beau Architects。“成为安迪·沃霍尔”这个展览,每个单元都有主题色,二层沿分割墙还放置了显示屏,它既是延伸,又打开了另一个视域。设计师陈小溪,在空间的中间部分,还摆放了几张银制沙发,观众坐下来,才能比较好地观看二层的影像。如果细看的话,这个展览的每个小角落,都发现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我对拍照打卡这种行为大体上是接受的。这两年,拍照打卡几乎成了很多观众看展的目的,这其实反映了整个观看行为的变化,不见得说,拍照打卡有多么低级。进一步说,拍照打卡也是观众与美术馆、观看与策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沟通,美术馆和策展人可以从拍照打卡内容上得到非常即时和根本的反馈,这种现象以前没有。这种沟通,会直接反馈到下一个展览,很多有趣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会慢慢浮现。
展览不就是为观众服务的吗?我比较希望看展实实在在成为一桩享受,一桩日常的舒适体验。比如说,毕加索大展期间,很多观众会反馈,展厅很冷,看一圈感觉很累,后来我们就做了针对性的调整和设计。
南方周末: 每年,UCCA的公共项目都有上百场,形式越来越多样,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这在诸多美术馆中似乎比较少见。为什么UCCA坚持做公共项目?
田霏宇:UCCA做公共项目基本的出发点有两个:一个是触达观众,比如以新方式推广展览。另一个是和其他文化领域建立比较开阔的连接和来往。展览的容量有限,2021年北京、上海、北戴河三个地方加起来,一年也只有十二个展。而我们仍然有想要探索的问题,有我们想要探索的方式。我们做很多公共项目的意义也是回应我们越来越多元的需求,它也是UCCA核心理念的一部分。
和公共项目相关的还有艺术教育。现在中国的艺术教育,很大一部分是由博物馆、美术馆来承担的。除了基本的艺术教育之外,博物馆、美术馆现在几乎是最好的艺术教育途径或者方法。相比较教科书、兴趣班,博物馆、美术馆的优点也很明显。UCCA每年都会对全国很多城市的教师进行培训。前不久,我还和刘小东一起回到了他的老家辽宁省锦州市,实地进行艺术教育。
UCCA还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导览系统。我们培养了几百上千的导览员团队,这些导览员每天都会给很多观众解说、导览。威廉·肯特里奇的大展期间,我们的导览员都会穿上定制的T恤,上面写着“Ask me”。导览员比较专业也比较私人的解说,基本上覆盖了很多常规解说词无法覆盖到的东西,很多见解、情感、认知都是在倾听导览、和导览员的互动中产生的。我相信,未来中国的美术馆的导览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张朝贝、颜雯迪、李摩桉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