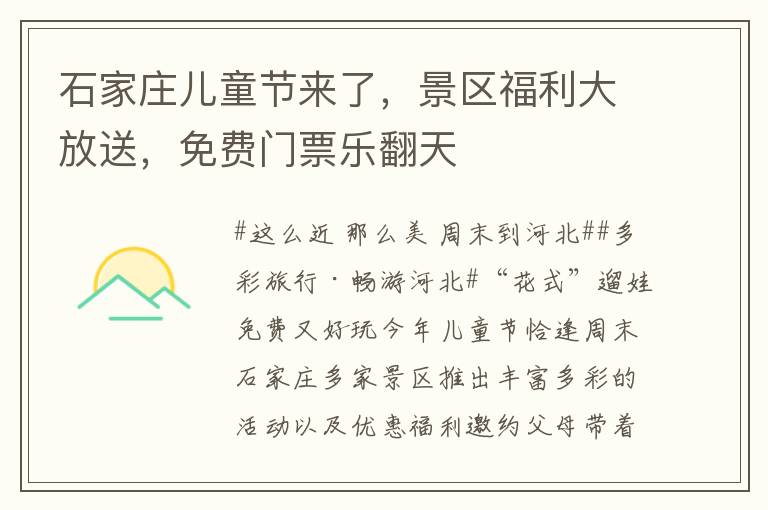真惨,娄烨导演的新片《兰心大剧院》,尽管有堪称顶配的阵容——
巩俐、赵又廷、小田切让、张颂文……还是市场遇冷了。

上映近一周,票房不过1800万,甚至快被点映的《不速来客》赶超。
今天,飘不主谈电影。
而是想借片中的演员王传君,来聊聊一类群体。
国产大女主角电影里,性压抑的小男人们。
或许,这类角色将成为内娱小生转型实力派的新赛道。


(注:该章节涉及部分剧透,介意请跳读)
《兰心大剧院》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12月底,聚焦孤岛时期的上海。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周,著名演员于堇(巩俐 饰)大张旗鼓回到危城。
目的成谜。
引来多方注目。
其中便有王传君饰演的莫之因。

同片中大多数角色一样,他身份也不简单。
既是谭呐(赵又廷 饰)戏剧的制片人,又是汪伪政府情报员,同时暗地里还和日本军方密切往来。
简而言之,留着汉奸头、西装革履的他,是标准意义上的反派,是“一个变态”。
这一非常容易标签平面化的人物,却在导演娄烨与演员王传君的共同作用下,释放出不一样的滋味。
而进入他的关键词,是欲望,是他与白云裳(黄湘丽 饰)的纠缠。
最初,白云裳打着粉丝旗号,去接近于堇,想要一探究竟。
知道她是**情报员的莫之因,就此想要套近乎。
车内,面对年轻貌美的白云裳,他先诱之以利,又妄图动之以色。
一面,倾身靠在她耳边,呢喃着:“跟我合作吧,我让你舒服。”
一面,不等对方回复,手底下就开始不老实。
然而,白云裳却毫不容情地,狠狠扇了他一巴掌,力度大到眼镜都快被打落。
当此大辱,莫之因一言不发。
只是把眼镜拿在手里,埋头看了看。
收住眼底汹涌的情绪,再扭头望了白云裳一眼。

她冷冷说了句:“开车。”
他便带上眼镜,扶好帽子。
只抽了几下鼻子,“嗯”了一声,依言发动汽车。
不管外表如何体面光鲜,其实莫之因的内里,不过是色厉内荏的小赤佬。
哪怕顶着制片人名头,因卖国求荣的行径,剧团里众人皆看他不起。
他身上裹着厚重的毛皮大衣,却撑不起想一展雄风的羸弱身板。
他对白云裳的欲望,不是男人对女人的爱欲。
而是,欲图通过征服这个高傲的女人,来证明自己可以。
是想通过占有女人的阴道,来满足自己对权欲的渴望。
所以他威胁、强暴白云裳时,要反复逼问:
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吧
色意伐(刺激吧)

他骨子里,深深刻着自卑的基因。
才要在最像男人的时刻,还要反复追索答案。
才只能借强权之手,以强迫手段达到心理与生理的双重高潮。
就像回到了前不久的晚宴。
他被同剧团的演员推搡。
他点头哈腰地对日本军人报上自己的名字,却换来一句:“谁他妈在乎啊。”
此刻,在进入白云裳身体的那几分钟里,他暂时地抛却掉那些不堪的记忆。
白云裳、于堇、谭呐……那些瞧不起他的戏子们,都被他压在身下。

“一旦暴力进入剧场,演戏的和看戏的无一幸免。”
娄烨说。
在剧场后台上演的这幕暴力,能把所有人吞没与摧毁。
王传君饰演的莫之因,既是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人。
又是广义的、抽象的符号。
它的名字叫——欲望。


熟悉娄烨的影迷都知道,他标志性的手持摄像,既出于对“记录式摄影”的个人追求,也是为了保证表演的自由度。
《兰心大剧院》的剧本是开放的,没有规定演员具体的动作与台词。
导演指导演员时,“不是按照符号和身份来进入角色,而是从很具体的东西出发”。
比如,这个人物的前史如何,和其他人的关系如何。
它们不会出现在电影里,却是去掉好与坏的符号,建构起“人”的开始。
王传君说娄烨的口头禅是“随便”,拍他的电影自由度非常大。
可以舒展全方位的自由,对好演员是酣畅淋漓的释放,是能够与对方棋逢对手的较量。
对不够好的演员,则意味着无所适从,甚至是对职业信心的摧毁。
还好,尽管这次只是个八番的配角,王传君不光在有限空间内接住了戏,还能让人琢磨余味。
从昔日的关谷神奇走到如今——
飘私以为,对他而言最重要的转折点,来自另一个色欲满满的配角:《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的马仔。
满脑子都是“家伙和女人”的马仔,下流却仗义。
会一脸窥视欲地打量他带的小弟,用上海腔调问他“弄过吗”,嘲笑他“还是个童子鸡啊”。
但也会自掏腰包,给小弟寻找能帮他“弄一下”的女人。
可惜马仔死得早,统共亮相三场,被乱枪扫射时电影才进行到四分之一。
但他的生与死间接开启了另一个人的觉醒:杜江饰演的“童子鸡”。
说间接,是因为飘认为,让“童子鸡”苏醒的直接因素,是女人。
“童子鸡”是从江浙地区来上海的乡下人,老家还有个等他回去结婚的“相好”。
他出来闯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站稳脚跟,赚够钱。
他对世事懵懵懂懂,时常露出天真的憨笑。
哪怕被朋友嘲笑是“小鸡鸡”,也只会收住笑,低下头默默不语。
但靠前次杀人,他又那么凶狠不要命。
是由于当时支撑他的一切力量,就是求生,就是赚钱。
他要证明自己不是“童子鸡”。
但当性不可得时,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来彰显荷尔蒙。
当血飞溅到他面上时,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靠前步。
第二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是性。
从大屠杀中侥幸逃生的“童子鸡”,中枪后苏醒过来,恍恍惚惚中,去了王传君为他找的、帮他开苞的妓女霍思燕那里。
淌着血,在霍思燕床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一宿。
这是导演程耳对杜江讲戏较多的一场。
他要杜江对着霍思燕,露出一个微妙且暧昧的表情来。
程耳告诉他,在那一刻,童子鸡突然觉得很舒服,有点忘记了自己身上的伤,有点释怀,心想今天也许会死在这里吧。
临死前看到一个曼妙的女性身体隐隐约约在珠帘背后,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慰。
来源 | 橘子娱乐
这场戏从早上拍到深夜。
“童子鸡”的脸上,首次有了裂缝。
你看他慢慢坐下来,一点点倚靠到身后的墙上。
从茫然,再到豁然,隐隐含了笑意。
仿佛世界洞开,窥见了人间的大秘密与大欢喜。
这才有了后来霍思燕照顾重伤的他,他醒来后赖在了霍思燕那儿。
霍思燕叫他回老家,寻相好的结婚。
他说他老早就忘了。
霍思燕眼里汪着泪,抱怨他伤好了,还留在这儿做啥。
他说他“上瘾了”“离不开你了”。
直到抛出他对她能做出的终极承诺:“我养你。”
冷血杀手蜕变为养家男人,看似是被女人迷了魂。
实则他的眼神,有了前所未有的坚定。
原本模糊不清的未来,在遇到这个女人,在与她有了肌肤之亲后,终于呈现清晰的轮廓。
他看到了人原来除了走别人安排好的路,还可以有另一种活法。
他明白了成为男人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你杀了多少人,赚了多少钱。
而是肩负责任,并愿为之矢志奋斗。
发现没,莫之因也好,“童子鸡”也罢,这些男人的转变,或多或少都与女人相关。
所以王传君在《罗曼蒂克消亡史》里戏言:“弄一弄,你的经络就通了,就会发现以前的日子都白活了。”
笛卡尔曾说:“爱会影响你的脉搏和胃口。”
性亦如此。
它从来不止关乎“性”,而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脉搏和胃口。
表达人们对生命感知的最复杂的原始冲动。
唯有赤裸裸地直面、反观自我的内在欲望,才能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因此,复杂的性也成为电影里,折射社会世态的一扇窗。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是许多港人心中的“黄金年代”。
随着女性经济与社会地位皎如日出升起,男人日渐被反衬得黯淡、无光。
男性普遍焦虑的背景下,港式中产喜剧片中,批量生产出一波“小男人电影”。
图源 |《小男人周记》
片中那些“小男人”们,自卑,呷醋,处处失势,乃至性无能。
甚至标准爱情喜剧如《孤男寡女》中,都安排了让刘德华吃牛鞭的隐喻。
类似的情况到了这几年的国产片里,就是大女人戏里,那些欲望被压抑的男人们。
相比作为主菜、光鲜帅气的男主角,这类角色往往只是一例配菜。
但人性深层欲望勾出的丰沛与复杂,赋予了他们相对自由的创作。
让他们能跳出完美却相似的角色,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尤其这两年国产大片里,中生代演员多在主旋律战争片或奇幻电影里打转。
不是说这类题材不好,而是置身其中的演员,往往负责的是功能性叙事,是靠树立英雄来满足观众的想象。
比如杜江,在《红海行动》后,俨然成为“主旋律小生”的热门人选。
但他最有记忆度的角色,对飘而言,仍停留在“童子鸡”那里。
还有接连在《八佰》《金刚川》《**者》中亮相的李九霄。
刀子之类的角色,在群像电影有限的戏份里,给予观众较多的印象,不外乎“热血”“燃”“帅”等关键词。
反观《送我上青云》里他饰演的四毛。
一番云雨后,他躺下休息,却听到身旁姚晨自我愉悦的呻吟。
曾吹嘘自己“很厉害”的肥皂泡,就在声声叫嚷里破碎——
女人的满足,居然不是靠他,而是靠自己完成。
被伤了男人自尊的四毛,起身,望住姚晨三秒,躺回原处。
那三秒中眼里涌动的情绪,胜过之后所有的言语。
性是私密的,是个人的,是难以言说的。
同时,它又是流动的,是多元的。
关乎自己与他者的关系,关乎自我在世界中的所处。
因此《性学观致》中才说:“性是一个生物学功能,但它只有通过社会化才能获得其形式和意义。所有的文化都影响着性行为,但方式各不相同。”
具体到表演方法上。
哪怕是和同一个对象,在不同感情阶段,都会有各异的表达。
所以李安在拍《色,戒》每场激情戏前,都会私下和梁朝伟沟通,把要求的每个镜头都说清楚。
让演员知道他做的每个动作,都有不同的动机、意义、心境与感情。
如此,激情戏才成为一双眼,让人看到易先生内心活动的外在化。
在满是“炸裂式演技”吹嘘的今天。
把握诸多复杂的层次,同时搭建好与对手戏演员的默契配合,才更是内娱小生演技的试金石。
够胆来试,或许这类角色就是他们以演员身份被人记住,渐渐翻红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