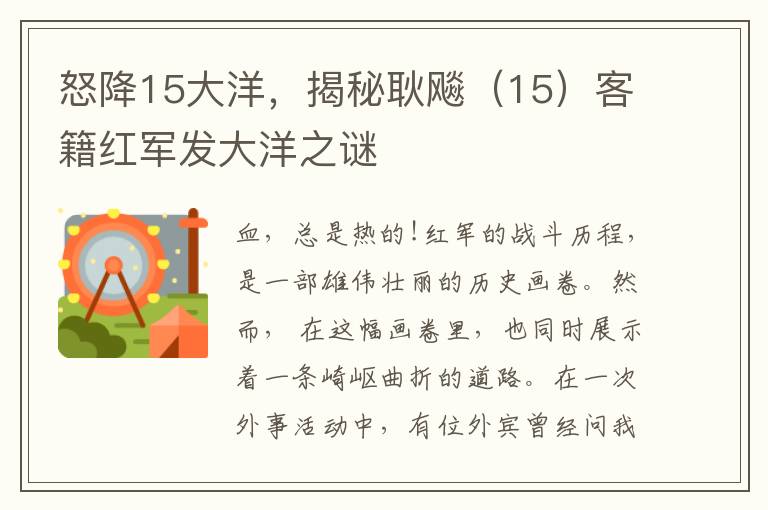
血,总是热的!
红军的战斗历程,是一部雄伟壮丽的历史画卷。然而, 在这幅画卷里,也同时展示着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
在一次外事活动中,有位外宾曾经问我:“阁下对那时的红军,受到内外两种打击,而没有溃散,将作何解释?”
我说:“你知道‘军心’和‘爱国心’这种凝聚力吗?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血,总是热的’这种观念吗?”
是的,当几万名以农民为主要成份聚集起来的热血青 年, 一夜之间成为士兵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军事常识,大概就是“军令如山”这句古话。
而当“军令如山”的纪律性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理 想”联系起来的时候,与中国的国家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的 时候,便产生了巨大的召唤力,这就是军心,这就是爱国心,这就是使人们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
然而,那时的党和军队,都处在初创时期, 一切都是幼 稚的、单纯的。由于“四·一二”事件中蒋介石举起屠刀,中 国共产党一夜之间被推入血海,使幼年时期的党处于更为 险恶的环境,加上党缺乏经验,以及少数领导人缺乏马列主义,就导致了一系列“左”倾错误。
我记得那是一九三〇年年底, 一个下着冷雨的深夜,我 们九师司令部的同志们都静静地躺在又凉又硬的门板上, 没有人翻身,没有人打呼噜,甚至连一声长长的叹气都没 有。但我们都没有睡着。因为,我们司令部的参谋长赵昆光同志,刚刚被拉出去……。罪名是 AB团。
在此之前是师部副官长, 一个文质彬彬的学生官,不愿 做地主少爷而跑出来当红军的四川青年。说他 是 AB 团,让他供出谁是同伙,他没有挺住那些刑具,嗫嚅 着说与赵昆光同志一起买过花生“打牙祭”。这个被称为“花生会”的“反动组织”就这样诞生了。
赵昆光同志是云南人,所以他与那个四川藉的副官长没有“同乡会”的嫌疑。但他做了“花生会”的第二位祭刀者。 赵参谋长在战场上是一员勇将,在司令部又是出色的“军 师”。他能在浏览一遍之后,把军委那些长长的命令向部属 一字不差地复诵出来。他在阵地上口述战斗命令,真有“多 一字则太长,少一字则太短”的技巧。他书法极好,签在文件上的“赵”字带着“八大山人”的狂劲。徐彦刚师长很欣赏他。
我对他甚至有些崇拜。我当参谋后经手的第一份战斗文书, 就是他手把手教我写成的。那次是徐师长给的任务,并嘱咐 我不会可以去请教参谋长。赵昆光同志热情地拿出纸、笔, 一边口述; 一边指导,把格式、要领, 一点一滴地讲解清楚, 甚至连复写四份这样的细节都交代清楚(因为有三个团,师 里留一份底稿)。之后,我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各种参谋业 务。就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壮志未酬,却饮恨九泉。
本来,在尖 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敌人总要想方设法,派出一些奸细、 特务,钻到革命队伍里来,搞内部破坏活动;而革命队伍本 身也不可能纯而又纯,总难免有少数投机分子混杂其中, 一 旦气候有变或形势紧张,这些人就可能干出不利于革命的 事。
因此,我们在对敌斗争的同时,对革命队伍进行整顿,这 是必要的。但是,整顿中必须重实据,实事求是,不能轻信口供,更不能以流言蜚语和挟嫌诬告者的谎言作为根据。
后来,这种极左思想的恶劣影响,却一直在党内和红军中存在 着。
例如,打仗的时候,必须直着身子不断地向前冲,不许弯 腰,不许掩蔽,不许停顿,不许利用地形地物来躲避迎面射 来的子弹和呼啸而下的炮弹。谁要躲避子弹,就算怕死、不 革命。
记得当时每个连、营或团等单位,都有一名“掌旗兵” 负责打红旗。掌旗兵全是百里挑一的英俊小伙,但是这种人死得最多。因为无论是他们掌着红旗在队伍最前面冲锋的 时候,或是护着红旗站在高处的时候,都不许弯腰,更不许 蹲下,这样,他们就成了敌人的活靶子。所以,仅从这一点 看,“左”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使我们无数的好战士作出了无谓的牺牲,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这种“左”的思维方式还表现在军事指挥上,且不说王 明、李德等搞的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和首先夺取“中心城 市”等战略性的错误,就是在具体的战斗中,当时红军的战 术词汇里,也只有“前进”“胜利”,不允许讲“退却”“失利”。 那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连什么是宏观的战斗口号、什么是实际的战斗要求都分不清。他们向几千里外战场上的红军发出一封封的“长电”,一厢情愿地部署兵力,规定着“赤化”这里,“赤化”那里的时间。
当共产国际代表、军事顾问李德到达苏区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甚至连哪条战壕里放几个兵,迫击炮应当架在哪条等高线上,都做了硬性规定。
藤田整编后,我曾到一军团一师三团任过一段时间参谋长。当时正是一军团奉命实行“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方针, 辗转于敌人堡垒与重兵之间死拼硬打的时期。
三团奉命在棠阴附近突破敌人封锁线,北上袭击敌人。我们先打了云盖山守敌,打得十分艰苦。战斗中接到命令,让我们冲到大雄 关东南某地去占领制高点,策应主力突围,并临时受二师指 挥。
在经过一个三岔路口时,我发现这地方实际上是个葫芦 形的隘口,如果两边的高地被占领,这个隘口就会成为一个 进不来、出不去的“卡子”。我带着尖兵走到这里后,赶紧停 下,派通信员请团长黄永胜、政委邓华上来一下,建议派一 个营守住这个口子。
黄永胜不同意,只是一个劲地下令:往 前冲!我说,冲得上去便罢,倘若冲击失利,需要退回来怎么 办?
黄永胜说:“参谋长你想干什么?红军哪有‘退回来’的 道理?我们就是要前进。”前进,前进!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那时的战斗动员令里到处都充满了这种口号。最后我只好 行使参谋长的三次建议权,他才同意留一个连守口子。
结 果,主力前进之后,进攻受挫,死打硬拚,陷入重围。原来,和 我们交手的敌人,明里是一个营暗里还埋伏着三个营。这样,在兵力上我们处于劣势。打了一阵,看看有被围歼的危险,只好撤退。但是,退路上那个我曾建议控制的口子,因我 们留下的兵力过少,被敌人抢去了大部分阵地。敌人用机枪 一堵,差点使我们这个团全军覆没。幸好留守的这个连英勇善战,经过拚命阻击,才接应部分人脱险。
事后,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立即把我们三人找去, 一 向慢言细语的陈光师长大发雷霆,指着我们的鼻子质问: “打了大败仗!你们怎么搞的?”
在问明情况后,陈光师长说: “耿飚同志的建议是对的。”三天之后,我被调到四团去任团长。
红四团是在原叶挺独立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力团, 在北伐中素有铁军之称。八一起义后, 一直由朱德同志兼任 团长。在朱德同志不再兼任团长后,由肖桃明同志代理团 长,但是尚未下正式命令,他便牺牲了。
牺牲的原因说来痛 心。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时无论战斗员还是指挥员,在战场 上一律不得弯腰,否则便算“怕死”。四团居高临下与敌人作 战,肖桃明同志观察敌情时,正是因为使用了那种“不怕死”的姿势,很明显地暴露了目标,所以被敌人击中。
如果说,“左”倾机会主义对内部的危害使我们牺牲了 许多好同志;那么,在对待外部友军或可以争取的朋友的 关系上,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恶果。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 旬,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发动了震撼蒋家王朝的“福建 事变”。这本来是建立联合战线的极好时机,可是我们却采取了任其自然发展的姿态,以至错过了机会,使蒋介石从容地把十九路军消灭了。
就在蒋鼎文率领第三、第九两个师从南丰向闽西开进,准备去攻打十九路军时,我们一军团就在敌人进军的侧面山上休整。敌人在我们的枪口下毫无戒备地扬长而过。
我 们本来已把部队布置好了,想打它个措手不及。可是上面传 下命令:不准打!我们再三报告,说再不打就没有机会了。但是上面就是不让打,说什么十九路军是“第三势力,比蒋介石还坏”“是迷惑人的狐狸精”。
我在阵地上听到上面来的人 说:“‘大军阀’打‘小军阀’啦!让他们狗咬狗去吧!”这种“左”倾机会主义,实在是革命的一大祸害。
本来,南方各省的军阀对蒋介石都是怀有戒心的,如果 我们对“福建事变”处理得当,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一带的 军阀们,都有可能与我军联系,共同建立一条反蒋统一战 线。但我们在“福建事变”中的作法,使他们失望,我们自己 则丢了威信,导致各地军阀纷纷向蒋介石靠拢。在以后的长征路上这些军阀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对我军围追堵截,使我们吃尽了苦头。
在接二连三的反“围剿”战斗中,环境的艰苦是令人难 以置信的。但红军的指挥员和战士,大都是十几、二十几岁 的年轻人,充满革命的朝气。所以,尽管受到敌人的“围剿”和内部“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我们的生活还是十分充实。
我们驻在小布的时候,苏区实行优待红军的政策,那大概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优抚政策。当时,地方苏维埃把红军人员分为“本省红军”和“客籍红军”。本省红军指江西籍 的红军,他们的家中都按规定分得一份土地,由苏维埃代 耕。
像我们这些由外省来的红军,即客籍红军,便发给一定数量的大洋, 一般是十块钱,以贴补家用。我是湖南人,享受客籍红军待遇,但由于家乡还是白区,无法把钱捎回去。而 且,部队天天忙于行军打仗,环境艰苦,这些钱我都用于照 顾了伤、病员和接济贫苦老乡了。
记得小时候父亲告诉我, 人缺了盐便没有力气,我唯一的花销是经常买点盐巴,用一 个小瓶装好带在身上。那时常常发生“青菜和水煮”的情况, 这种时候能有点盐巴,就算是很好的享受了。
一九三三年我 们打完草台岗战斗,中央红军实行整编,我拿出一块钱买了 两只老母鸡,煮熟后请黄姓政委一起来吃。当时什么佐料也没有,只有我的半瓶盐巴,可吃起来比吃宴席还有滋味。多少年后,我们还记得那顿只有盐巴的“白斩鸡”。
藤田改编时,我们一、三、五军团凑在一起。平时虽然互 相慕名,但没有机会见面。那次各路指战员会师,气氛相当 热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陈赓同志,大家都愿和他在一起。陈赓同志无论在我方还是国民党那边,都很有名气。
那次我们在会后举行会餐,陈赓同志和我同桌。他见上来一盆 肉,就迅速地把肉全分到我们碗里,然后把盆子藏起来,咋唬说:“喂,大师傅!我们这一桌还没有肉哪!”伙房里果然又 送来一盆,这时他便似乎没注意地把“谜底”(藏起来的盆子)露了出来,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他那次还讲了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八一”起义时,他腿部负伤、撤到厦门,由于怕敌 人认出他是伤兵,便躲在一个厕所里,让警卫员卢冬生去叫 一桌西餐来吃,结果西餐没吃成,反被店家臭骂一通。他讲这些艰难的经历时,总是带上一层喜剧色彩,充满了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
当时,我们最“红火”的文化生活是开联欢会。军、师、团都有宣传队,任务是做行军打仗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人数不多,但十分活跃。每有各部队之间的联欢,他们便成了主 角。
尤其是师以上的宣传队,编制上有女同志,三、五个到十 来个不等,她们的节目最受欢迎。每次联欢都有领导上台, 有时是清一色的指挥员登台演出。
我记得有一次, 一方面军 的黄镇同志还是彭加仑同志,编了一个话剧,有点像现在的 活报剧。大意是:蒋介石开会派兵,布置大军围剿红军,结果 仗打败了,蒋介石气急败坏,把自己的头打破了。
扮演蒋介 石需要一个瘦高个,不知谁推荐我担任,李克农同志便来动 员我上台。我说行,但剃光头我不干,他说不剃光头不象啊,我说让罗局长(即罗瑞卿)去,他的外号是“罗长子”嘛。后来罗瑞卿同志不知怎么把林彪动员上台了。
我那时拿手好戏是与胡迪同志一起演双簧。他在幕后, 我在台前。胡迪同志是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台长,可算是我 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开山鼻祖了。我们的节目通常是表现 红军战士作战的。他在幕后发出各种战斗时的声音,我在台上表演临战中的单兵动作,我们配合默契,演得十分逼真。
但有时也出“洋相”。比如,我在台上向敌人“射击”,他在台 后看到我扣“板机”却有意不发出“叭”的射击声,我只好回 头看他一眼,他作手势让我捅捅“枪管”,我刚把“枪”倒过 来,他却突然“叭”地让“枪”响了,于是我“自己打死了自己”,引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
有“传统节目”的还有肖劲光同志,他的著名表演是“高 加索舞”,因为他刚从苏联留学回来,这种舞有点“踢踏舞” 的韵味,表演多了,大家都学会“劈劈叭叭”地给他拍巴掌伴 奏。
为了演这个节目,肖劲光同志还专门准备了一双长筒皮 靴。这个舞别人是跳不来的。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刚刚由 宁都起义过来的时候,实在没有节目,便让部下一个团长代 劳,表演北方拳术,后来又增加一个大刀对打。我从武术角 度看,打得确实不错。这种官兵同乐的文化活动,我们一直保持到长征、陕北和解放战争时期。
最令我们高兴的是每次打完胜仗,大家讲战斗中的见 闻。其中有许多故事后来都写在书中。解放后,有一次过 “六一”,少年儿童约我讲个红军故事,我就讲了一次打“红 枪会”的经历。
那是一九三二年六月,我们从漳州回师江西, 在途中打“土围子”。有的“土围子”带有迷信色彩和帮会性 质,反动派利用它们来骚扰红军。“红枪会”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支清一色使用梭镖的帮会武装,每支梭镖上都有一 簇红缨,所以叫“红枪会”。
当时我是红九师参谋长,听通信员报告说有一个连被“红枪会”围住了。我赶到现场一看,红枪会的人正在那里祭坛哩。他们点上几堆火, 一个个都赤了 膊,先杀一只鸡开戒,饮过鸡血酒,就把鸡毛拔下来,每人在头上帕子里插上几根。所有人的脸上都用五颜六色的油彩涂成鬼怪脸谱。然后,他们的“法师”便踏罡布斗,“叭呢叫”地念一通咒,他们的人似乎便“刀枪不入”了。祭坛完毕,每二十人一排,间隔十来米再上一排,列成横队向我们杀来。
连队把我叫来的意图是请示一下怎么办。因为“红枪 会”里大部分是受骗的穷人,打了于心不忍,但是他们受反 动派利用,不打则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杀我们。
我马上召集各 班长开会,讲明:
第一,立即组织喊话,让他们明白穷人不打 穷人,“刀枪不入”是鬼话;
第二,组织神枪手拣首恶的歼灭, 一是打破“刀枪不入”的迷信,二是惩办反动骨干;
第三,万不得已时,将第一排、第二排击伤,同时大造声势,吓跑了事。
我们的喊话没起多少作用,因为“红枪会”的“神兵”们 嘴里不停“喝”“嚼”地发着威,根本听不见我们喊什么,只是 瞪着大眼,端着红缨枪往上冲。
我们十几个神枪手便打出第 一排子弹,神兵里中弹的有的扔掉红缨枪,捂着伤口喊娘, 有的扭头就跑,其余的原地站住,不知怎么办才好。
我们再 向第二排神兵打一排枪,彻底打破了“刀枪不入”的神话。神 兵乱了营,我们便吹起冲锋号, 一个冲锋,把“红枪会”赶得 远远的。按照红军的俘虏政策,我们把受伤的“神兵”包扎治疗,送到他们的家里,让他们自己去做宣传,这些“土围子”就这样被瓦解了。像“红枪会”这种靠欺骗胁迫群众打红军的事,毕竟是极少数。
在我们经过的地方,红军与人民鱼水情深,亲如一 家。部队每有任务,百姓箪食壶浆,夏天无论妇孺,人手一 扇,在路边为红军扇凉,冬天支起大锅,为红军送上热茶,到处都有送郎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在漳州时, 一位贫苦的老阿妈,牵着她年轻媳妇的手, 一定要我们收下当红军。原来,她的儿子当了红军,在战斗中牺牲了,老人家便让媳妇从军,完成儿子未竟的事业。后来,这个女同志编到红三团去了。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的人民群众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在红军长征前夕,我带领四团驻在江西于都,团部设在一户普通农民的家里。 一连几天,我发现房东一家总是躲在 窗后,反复地打量我。开始我并没在意,后来,这家房东开始 向站岗的哨兵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家在哪里。由于我是团长,哨兵不能贸然透露,于是,房东直接找我询问了。
原来,这户人家的儿子,五年前当红军走了, 一直没有 音信。这位同志是新婚才三天参军的,他的父母亲、妻子,不 知怎么认为我就是那位同志。于是发生了一场“认亲”的事件。
那天刘亚楼政委到我们团部来,检查我们的出发准备。 房东老伯、老妈妈、大嫂进屋后,杨成武同志出面接待。我断断续续听见说,他们是从兴国搬来。
过了一会儿,杨成武同志进来,才告诉我他们是来认儿子、丈夫的。他们说的年龄、 相貌都与我相似,但是姓氏、籍贯不对。刘亚楼同志便让我 与他们直接见面,我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立即使他们明白了真相,这才结束了“认亲”事件。
不久前,我在青年女作家何晓鲁同志写的一篇文章里 看到,江西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奉献二十五万优秀儿女的巨 大牺牲——还不包括那些无名可查以及全家杀尽无人向政 府报数的烈士。后来我不知道这家房东是否寻到了他们的亲人。但是,苏区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将使我们永远追怀。
正是这些可歌可泣的战友和人民,使我们认定了革命的道路,并坚决地走下去。






